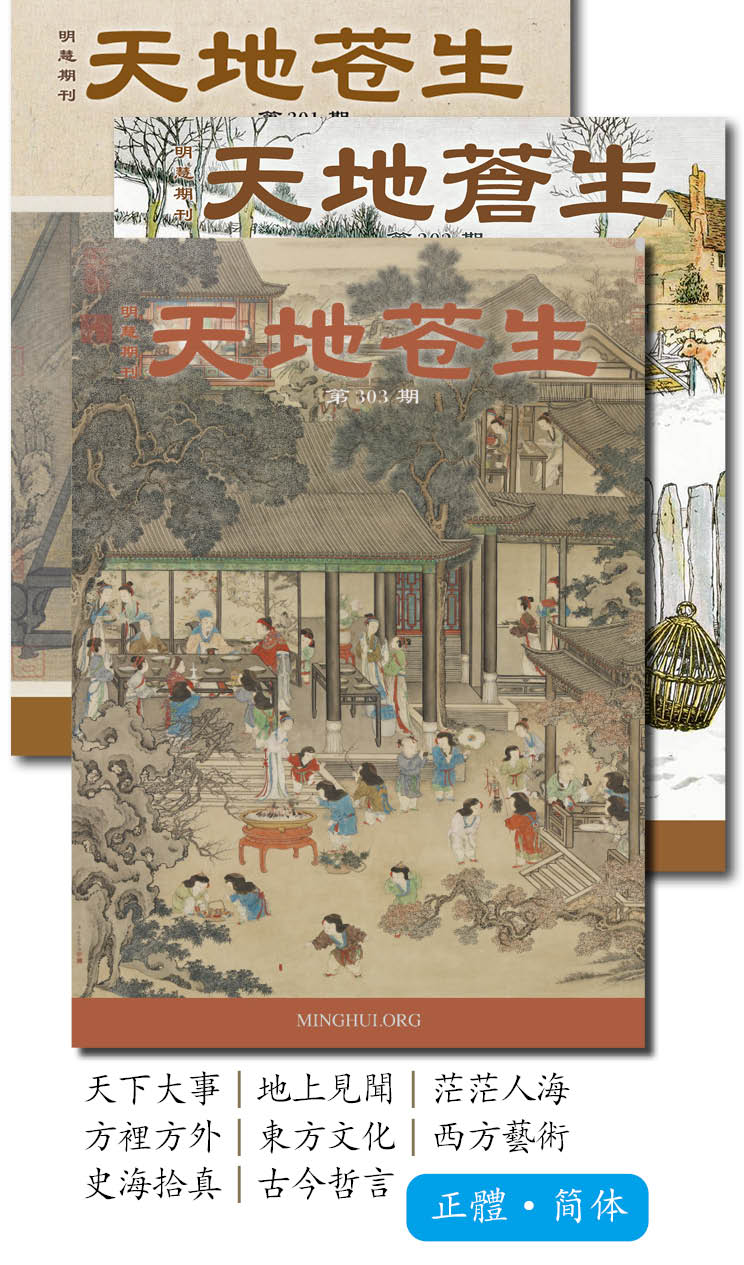广东高州刘惠荣自述遭受的迫害
自从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以来,刘惠荣和家人就过着担惊受怕的生活。刘惠荣自己曾经被迫害十几次,家人也受到恐吓和株连。其二姐因为她不“转化”而不能升职。中共邪党还恐吓其两个妹妹,如果刘惠荣不“转化”她们的儿女就不能上大学或不能当兵等。
下面是刘惠荣自述被迫害的经过。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迫害法轮功后,我经常被无故非法关押。当时身体还不是很好,走路困难,全身浮肿,虽然是好转了,但还未康复。
高州河西派出所比其它派出所邪恶,只要他们上级有活动,就先把我们法轮功学员绑架关押,时间不等。比如江泽民来高州,我和本村的几个法轮功学员都被河西派出所的警察提前绑架,非法关押在招待所一间房间里,不给饭吃,天天是妹妹送饭,一群保安守着,直到江泽民离开高州才放人,共七天。李长春路过高州时我们又被非法关押几天。
有一次在家门前见到一姓谭的学员夫妇散步路过,人之常情,请他俩到家里坐,一杯水还没有喝,我和姓谭的学员夫妇就被河西派出所的警察绑架,并分开“审讯”,关押二十四小时放回家,搞得人心惶惶。因为我家门前屋后都有便衣和保安蹲坑。
“七二零”后我和其他法轮功学员继续在公园炼功,被高州警察抓走,当时有学员被警察打,我们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在戒毒所十五天,十五天内勒索家人给一百二十五元饭钱。
那段日子真是度日如年。家人整天提心吊胆,担惊受怕。河西派出所的警察天天到我家来骚扰,所长张嘉义带队,一群警察有时早上天还没有亮就来了,有时上午、有时中午、有时下午、有时半夜,时间不等,还安排一个叫钟克志的保安专门到我家来“上班”。天天早上七点半就到,吓得我家妹妹的小孩哭。我叫他到外面去,使我家人抱怨我。
那时我的心很沉重,也很无奈,不知怎样好,当我得知很多法轮功学员去北京上访,要讲清法轮功真相时很感动,自己也决定去上访。
一天早上,我很早就背着行李向北京出发了。因天亮警察会来我家的。一路上想着到北京后怎样跟上级领导讲清法轮功真相。在北京西站下火车我就上了一辆公巴,先到天安门,在广场上看见很多警车呼叫。有警察问我是不是炼法轮功的,我说是,马上背后就被打了一掌,并抓上车拉去一个地下集中营,抄了我身上带的钱,将我和其她上访的法轮功学员一起关押。在那里呆了三天,茂名一科的警察将我押回转给高州河西派出所,河西派出所的警察将我先关押在一个黑黑的屋里,第二天严刑“审讯”。之后将我送到戒毒所拘留十五天,出来前也是要家人给了一百二十五元饭钱,纸巾钱另计。戒毒所里给我们的饭很难吃,菜基本上是吃黄豆。
经常被抄家,家人被吓得不象样,还要面对不明真相的人说三道四,指指点点,心理压力很大,精神受到严重伤害,我理解家人的痛苦,但家人不理解,说我自私,要我放弃。
有一次我出去买一些日用品,去的时间长一些,回来家又被抄了。看见家人害怕痛苦的样子,我心里很难过。这次河西派出所警察在我家抄家时,在缝纫机肚里找到一张经文,同时也抄其他法轮功学员的家,家里有大法资料的法轮功学员全被非法劳教二年。上午非法抄家时没有抓到我,下午又来。我在家反锁不开门,河西派出所的警察和“六一零”、国保、街道办的人就留下守着我家门口,有的回派出所拿工具、梯子来,准备砸门和上楼顶绑架我。我在他们回去拿工具时从楼顶走掉了,回头看我家楼顶有很多警察。
我在家不能呆了,就再次上京上访。在火车上遇见很多法轮功学员,当火车在河唇停车时,我们就转到其它的车去,到涞水检查身份证时我们被扣押在涞水派出所。警察得知我们是法轮功学员,就非法搜身,抄走身上的钱。我们在那里被关了一晚,被通知的茂名驻京办事处的人来接。我们要求给回我们的钱,自己买车票回家,警察不同意,我们就不愿跟他们走,结果被毒打。“审讯”时也打过。茂名驻京办的人强行把我们拉上车,送往茂名驻京办事处四楼关押。在房里我们十三人就反锁,要求还给我们的钱自己回家,明知他们不会善待我们的。
在窗口我们打横幅,叫“真、善、忍好,法轮大法好,还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背着《洪吟》〈无存〉。到凌晨天还没亮,他们就开始砸门,外面叫来消防车升起云梯,也挂起气垫,气垫是没有打结扎稳的。我们看见有气垫就想跳下去找机会跑,不能落在他们手上,结果就出现了北京跳楼事件(明慧已经报道)。
因为气垫的绳子没有打结,我们跳下去摔得不同程度的伤,有骨折的、有断腰椎骨的,还有一个当场死亡。我当时不省人事,醒后脑震荡,头晕的不能站,左手抬不起,肋骨痛得要命。在这样的情况下,第二天警察把我们押回高州,在火车上警察把我们两个一对的铐着,睡、坐都困难。回高州后将我们分开在各个派出所“审讯”,我在河西派出所几天几夜不给睡觉,警察轮班看守“严审”,不知过了几天将我关在黑房里,在黑房里又呆了几天就送去高州市第二看守所关押。在看守所里我们都有伤,忍着痛天天做奴工灯饰,不完成任务不给睡,没地方够睡我和几个法轮功学员就睡在地上。
二零零零年除夕前,警察把我们法轮功学员用车拉到观山招待所,领来一帮从三水劳教所来的所谓“帮教”人员,想“转化”我们。当时有几个“转化”的当晚就回家了,没有“转化”的后来转去高州市第一看守所,并非法判刑,三到七年不等,我被非法判刑三年。
我在非法关押期间身体状况恶化,不能炼功肾病严重,全身水肿,不能吃东西,走路困难,还要天天做灯饰,要求任务减半都不同意。后来就被迫害到大、小便拉水,身体又变成皮包骨,不能走路,连四肢都不会动,象个活死人。拉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我生命危险,各个项目指标都不正常,很严重了,活不了几天了。在医院打点滴,我一打点滴身体就抽筋,呼吸就困难。回到看守所的什么事情都要找其他被关的法轮功学员帮忙,学员要求警察放人,不然我会死在里面的。这种情况下,高州市各级官员到看守所来看我,看见情况属实,还要我写保证书才可以搞保外就医。我不同意写,怎知他们叫我亲人写了。
我回家后身体很差,妹妹不放心将我接到二妹家送广州南方医院治疗。“六一零”和国保人员要了我妹妹家的电话联系跟踪。有天打电话叫我在某日某时必须回高州市第一看守所报到。我回家按时到一所报到,怎知他们是叫我回来开宣判大会的,当着各中、小学的学生,还有群众的面宣判我们刑期,开完会后我们就被用车拉去游街示众侮辱。
二零零八年,我和法轮功学员去高州谢鸡镇义山村发法轮功真相资料,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谢鸡镇派出所的警察绑架我们转给高州“六一零”。他们拘留了我们十五天后又送茂名洗脑班迫害,直到开完奥运会才放回家,有六个月。
二零零八年四月份,高州“六一零”伙同国保、宝光街道办的人来我家绑架我去洗脑班迫害。我在里面炼功,被他们几个人冲入房间将我从床上拖下按在地上,双手向里反扭,向上抬,痛得我直叫。张冲云犹大在场不加阻拦,还在一旁幸灾乐祸。我双手被扭得抻不直,又肿又黑,双手手掌心和指尖出水向外滴。第二天他们假惺惺的问我要不要药水。我不理照常炼功,三个月后双手伸直才不痛,六个月回家。
二零一一年我又被绑架去洗脑班迫害,强制写了保证书一个月后放我回家。在这里我希望那些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早日清醒,不要做历史罪人,希望世人早日明白真相,停止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