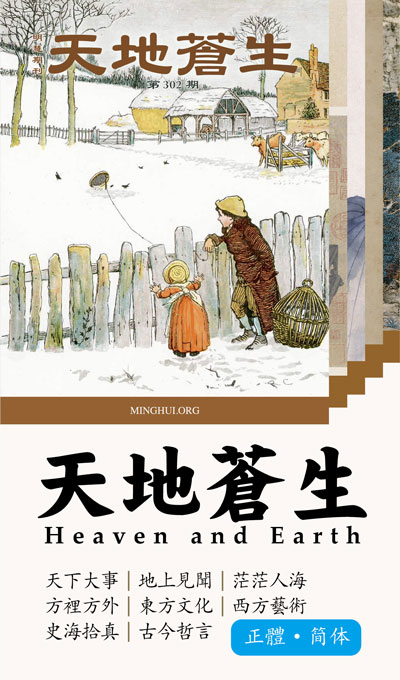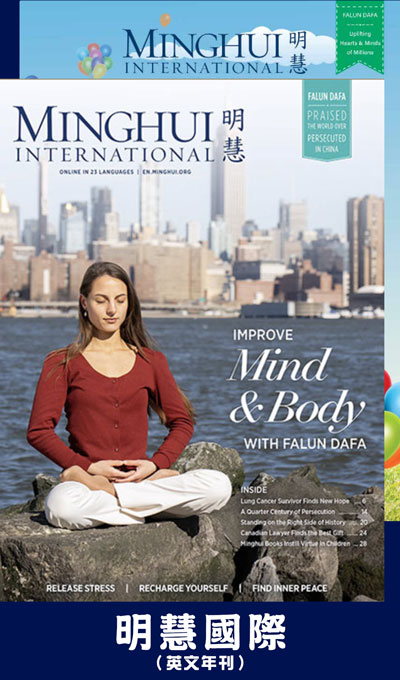吉林黄淑琴被迫流离失所三年多 家人长期遭骚扰
法轮功学员高万华被诬判三年,二零一七年前被送往长春吉林省女子监狱。
下面是黄淑琴女士自述遭迫害经历:
我是一九九七年修炼大法的,在修炼之前我身体 患有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胆囊炎、角膜炎、神经衰弱等多种疾病,尤其是胆囊炎怕累,农村活又多,稍干多一点就腹胀的不行,再加之其它疾病,造成恶性循环真是苦不堪言。三十几岁的我年年都要看病,药没少吃钱没少花,病根一个也没去掉。自一九九七年我有幸修炼法轮大法后,一身疾病全部消失。
法轮大法的法理也让我真正明白如何做一个好人,在大法真、善、忍的理念指导下我不再象以前一样,为了名利情与人勾心斗角伤害他人,更不会为了蝇头小利而乐而忧,尽可能的把方便和好处让给他人。在这种为人处世的理念下,我周围的环境变好了,我的家庭和睦了,我的身体健康了。法轮大法是高德大法!
正当我沐浴在法轮大法的佛恩中时,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泽民为了一己之私出于对大法师父的妒嫉,开始全面的对法轮功进行镇压,在灭绝政策的迫害下,无数家庭被抄,无数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拘留、劳教、判刑,整个中国处于红色恐怖之中,我也和所有的法轮功学员一样没有幸免,一次次的被关押迫害,不但给我本人的精神、肉体、经济上造成很大损失,而且给家人也带来无尽的痛苦。
一 、第一次被绑架
那是在一九九九年十月在我被绑架的头一天下午,当时我和丈夫正在吃饭,当地派出所(公主岭市秦家屯镇派出所)的警察常明磊(已遭恶报死亡),刘长春突然闯进我家,强行把我丈夫带到村上问话,因为我丈夫也修炼法轮功,(七二零曾经去过省政府上访在长春市大广拘留所被非法关押了半个月)。
我吃完饭两个多小时后,还不见丈夫回来,于是我也去了村上,可是到了那里一个人影也没见到,后来去问村长杜志金才知道丈夫因不放弃大法,被绑架到公主岭市拘留所。
得知这一消息,第二天在家里便给丈夫做棉裤准备送去。这时警察常明磊和刘长春又闯进我家说要调查我丈夫的案子,并且叫我有问必答。我告诉他们,炼法轮功的都是好人,常明磊一听立即翻了脸,厉声恐吓我说:你是不是也炼法轮功,炼就把你也带走。我坐在炕沿上看着年幼的孩子和年过半百的婆婆,心里非常难过,做好人说真话有什么错?却要被抓去坐牢。由于我不说假话,不出卖良心,不放弃大法,我被他们带上了警车。可是当警车行驶到半路时,突然听到我的脚下咔嚓咔嚓的响,并且震动的很厉害。这时常明磊开始骂我说:这一定是你们师父整的。他们把车开到了修理铺,一检查车底盘下面十二颗螺丝折了九颗,车坏了开不了了。他们只得下来押着我走去镇派出所。路上当有人看到我后边跟了两个警察,就问是怎么回事时,常明磊这个邪恶流氓却说她被人强奸了。对于上天的警示,他们毫无顾忌。
到了派出所他们象对待犯人一样对待我,强行做笔录,并且在没有任何法律的手续的情况下开了一张拘留我十五天的票子,然后又把我带到市公安局走同样的手续。当一个小警察得知我的丈夫也被绑架,家里孩子老人没人照顾时,随口说了一句那就给你开拘留七天的票子吧。就这样我被非法拘留了七天,我的丈夫被非法关押了一个月。
二、丈夫又遭迫害
我的丈夫是一个忠厚老实的人,当他看到我和婆婆因修炼了大法而身体健康了,因此他也走入了大法修炼。自从丈夫修炼了大法后,长期不愈的神经衰弱彻底消失了,以前连想都不敢想的力气活自从修炼之后都能干了,装满一百五、六十斤粮食的麻袋扛起就走。他按照师父教导的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村上不管是谁有困难,只要找到他,不管什么时候他都去帮,是村上有口皆碑的大好人。就连警察都对他说,你们村上的人对你评价不错。可是就是这样的好人却被无辜劳教迫害。
二零零零年的七月,正直抗旱时期,村上家家都用水泵浇地,每当哪家的水泵坏了,我丈夫都无偿的帮助修理。可是就在这时秦家屯派出所所长闫凯辉带领两个警察闯进村内,把村上所有炼法轮功的人集中到村上挨个问还炼不炼了,没有一个人说不炼。最后闫凯辉雇来一辆小客车把七名法轮功学员直接给拉到拘留所非法拘留,其中包括我和我的丈夫。
十五天之后,我和其他六个女学员被放回,一个月之后,我的丈夫被非法劳动教养一年,被留在拘留所养鸡烧锅炉做奴工。
就在丈夫被劳教期间,一天傍晚当地警察又来我家骚扰,当时只有孩子一人在家,当孩子听到剧烈的敲门声时,八岁的孩子被吓的钻到了床底下。
三、进京上访遭迫害
二零零零年的十二月,为给大法和师父说句公道话,我们当地同修一行七人决定去北京上访,在长春车站被非法扣押,后又在当地拘留所被非法关押二十三天之后,我被非法劳教一年,绑架到臭名昭著的吉林省长春市黑嘴子女子劳教所迫害。
到了劳教所先是搜身检查,第二天早上五点便起床,每个人被强迫坐在小板凳上,由一些邪悟的人散布污蔑大法和师父的歪理邪说,给每个新来的法轮功学员强迫洗脑,逼迫每个人写所谓的思想汇报。对于那些坚定不转化的,劳教所的警察利用各种酷刑折磨。
有一个叫周桂荣的女大学生(听别人说是长春人不到三十岁)因为拒绝所谓转化而绝食被扒光衣服,警察用手铐呈大字型把她固定在一张钢丝床上,身上只给盖了一个单子,没结过婚的人被下上导尿管,每天吃喝拉撒都在床上,还要被强迫灌食,由于长期躺在钢丝床上致使全身溃烂。
还有一个叫董秀凤老师的也因不转化,被劳教所的警察用电棍把脖子電成了焦糊状。还有的被锁在铁笼子里,在铁笼子只能蜷缩着身体。打骂是家常便饭,由于法轮功学员每天都生活在这种极度恐惧的压力下,精神承受到了极限,时不时的就有被逼的撞暖气片、甚至想结束生命的。
有一个叫孙丽杰的老师,被非法劳教三年。那年她三十一岁,由于承受不了巨大的精神压力违心的在所谓的保证书上签了字。有一天被管教孙明艳叫出去单独谈话,回来后一直闷闷不乐,没过几天,晚上梦中我突然听到几声怪叫,我们临铺的几个人同时被惊醒,就看孙丽杰在床上抖动了几下就没有了气息。同监室的人找来了医护人员做人工呼吸已经没救了。管教孙明艳到来之后草草的收拾了一下,然后撒谎说到医院抢救,并且威胁在场的法轮功学员不允许把此事说出去。孙丽杰死后她们连双鞋都不想给买,并且想要我的鞋给孙丽杰穿,我没答应她们无耻的要求。
后来听说那次警察孙明艳找孙丽杰谈话的内容是:孙明艳对孙丽杰说,对于老师上面有政策,如果说不炼了能提前回家,但是得送点人情钱。孙丽杰和丈夫刚刚结婚,而且丈夫被关在苇子沟劳教所刑期三年,在这种压力下孙丽杰心脏猝死。
在这种强大的恐怖压力下,我违心的妥协被强迫做奴工,有时最晚收工时间为凌晨一点,有时甚至到天明,超负荷的体力劳动使我和很多学员出现了头晕的症状,每个月六元钱的生活用品费对于经济条件差的学员还不够买卫生纸的。差十三天一年,我离开了这个魔窟。
四、被关洗脑班迫害
在中共邪党十六大召开前夕,也就是二零零二年,村上的治保主任王东华又闯到我家来要我和我丈夫的身份证,说怕我们去北京上访。我严厉的告诉他身份证不能随便收,另外我们出去打工还需要身份证呢。被我严词拒绝后,王东华气哼哼的扔下一句话:不给就给你们报告镇长鲁英军,然后走了。
傍晚时分,当地派出所把我们村上五个法轮功学员绑架到了公主岭市拘留所,也就是所谓的洗脑班。在那里我和三位女同修被非法关押了二十三天,我丈夫和另一位男同修一直绝食反迫害,一个月之后在我们强烈的要求下被放回。在参与这次迫害的村书记温海堂遭恶报骑摩托车腿被摔的露了骨头,因不醒悟一直参与迫害,已遭恶报被他人杀死。
五、再遭骚扰
二零零三年的春天,正值“非典”时期,一天半夜一点左右,我突然听到外面有人砸门,撩起窗帘一看,治保主任王东华领着几个警察在院子里,我没给他们开。他们见不给开从前门又转到后门砸,我叫起了丈夫和我母亲,还是没给他们开。
几个警察一起合伙开始拽门,我在屋里拼命的拽门也没拽住,门被他们拽坏了,我的手由于拽门被抻的脱臼变了形,直到现在还没完全恢复。他们象土匪一样疯狂的闯进屋内,把我培育的青菜秧苗给践踏死了一半。我怕他们这种流氓行为吓着母亲,拼命的拦着,他们却把我推的一个跟头又一个跟头的。其中当地派出所的所长申传伟闯到屋里后看到我丈夫在家,缓和了口气,其中还有一个女的翻翻这翻翻那的结果什么也没翻到。最后他们自己找了一个台阶说有一个逃犯和我丈夫重名,到我家是为了找逃犯。走之前扔下一句话说要我丈夫写个思想汇报明天交到村上去,我和丈夫一起说不能写。后来听说那天他们绑架了很多法轮功学员。
二零一一年,公主岭市国保队在“610”当时的主任赵兰平的指挥下又闯到我家来绑架我丈夫去洗脑班,在我强烈的反抗下,他们没带走我丈夫,一个陈姓警察打电话叫来了一辆黑色的依维客车,从车上跳下十六个黑衣特警,这时我的丈夫已正念走脱。又隔一天晚上,我和丈夫正在家里,他们怕住在后院的公公和婆婆阻拦将二位老人先反锁在屋内。他们撬坏了我家窗户,从窗户进来准备再一次绑架我丈夫,又被我赶了出去。这次他们不再绑架我丈夫,几个警察却将我按倒在地七手八脚的给我塞进了警车。这时我的公公从窗户跳出来眼看着我就要被带走,情急之下躺在了车前面,他们却不顾老人年岁已大,将老人拖到了一边,将我绑架到公主岭市响铃宾馆所谓的洗脑班迫害,到宾馆之后一个刑警狠狠的打了我一个嘴巴子,接着又从腰上抽下皮带,要用皮带打我。我心想我不欠你的,你不配打我。在我的正念之下他放下了手中的皮带,五天之后我被放回。
六、被迫流离失所
二零一六年八月七日公主岭国保队绑架了法轮功学员高万华,八日这天,我和当地一位学员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去了高万华家里,当时家里只有她的小孙子一人在家,孩子还没吃饭,屋子里面大法书和资料扔的满床都是,当我们刚想要给收拾收拾时,就听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正在看电视的孩子开了门,我们一看来的是市公安局国保队和刑警队的人,大约十个人左右。
进来之后,有几个警察开始抄家,他们不但抄走了大法书和资料,还抢走了高万华家值钱的东西(金银首饰、真相币)。另几个警察把我和同修带到客厅里训话,同修开始给他们讲真相,他们不但不听,还让我们俩人配合他们到派出所。两个警察先强行带走了同修,我不想被邪恶带走,于是趁着他们抄家不注意时光着脚一步两台阶往外跑,由于跑的太快,左脚被崴的粉碎性骨折摔倒。当我刚爬起时,被从楼下上来的国保队长钟民死死的抓住胳膊不放,当时我的胳膊就被他抓青了,钟民的五个手指印印到了我的胳膊上。我告诉他不要抓我,同时一甩胳膊,由于钟民抓我时用力太大,自己一下子摔倒在了地上。
当我拖着受伤的脚跑到外面时,我的右脚根骨移位骨头翻个,由于两只脚受伤,我再也站不起来了,随后又上来四个警察抻胳膊抻腿的把我强行拖进了警车,带到了公主岭河北派出所,刑警老李头和另一个警察把我拖进审讯室,我被锁到了一把铁椅子上,然后他们就去吃饭了。这一锁就是一下午的时间,当我告诉他们我想去卫生间又不能行走时,警察向国保队长钟民请示后才叫120救护车送我去医院。他们用担架把我抬到病房里,安排了四个特警轮番看着我,直到晚上九点多我的丈夫和家人才到来。当我想大小便时,就用布帘子挡上,警察就在布帘子的另一面,这种非正常人的待遇只有在中共执政的国家里才有。
我的双脚肿的吓人并呈黑紫色,双腿下部也变成了黑紫色,两天之后做了手术,左脚打上石膏,右脚打上了钢板和钢钉。每天还要打针输液,我不知他们给我用的什么药,自从输液之后我的腿上密密麻麻的长满了小红包,而且奇痒无比。当我的姐姐去问大夫给我用的什么药时,大夫抽了我一针管的血说拿去化验,可直到出院我也没得到结果。
就在我还没康复的情况下,河北派出所的警察就迫不及待的来所谓的提审,欲意构陷已被他们绑架的法轮功学员高万华并给我罗织罪名,我没配合。又一天的上午,国保队副队长徐志伟和一个警察又来到我住的病房,并且把病房翻了个遍,在没翻到任何他们所要东西之后,就回过头冲着照顾我的姐姐要她出去,他们有话要问我。他们问话的内容的和河北派出所的警察问的一样,又问了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话,我说我不知道,这时徐志伟翻了脸,叫着我的名字恶狠狠恐吓我说:“别看你现在啥也不说,我有的是办法整你。”我虽然从小就生长在农村,文化程度只有小学,但是我知道如何去敬老爱幼,尊重别人。面对眼前这种不公正的待遇,我的精神承受了极大的压力,我放声痛哭,此时我觉的只有这样才能释放我心中的郁闷。这时他们的恶行才有所收敛怕担责任,才叫我的姐姐来劝我。我的姐姐看到眼前的景象大声对他们说:我妹妹只是想帮人家照顾一下小孩子,现在被你们给弄成了这样,炼法轮功的都是好人,大马路上有钱谁都会去捡,炼法轮功的不会去捡,要都学法轮功这世界就好了,就不会有象你们这样的坏人了。在我姐姐的正义呵斥下他们走了。
由于他们不再给我交医药费并且还不放我回家,主治医师黑着脸告诉我说:我们这里不是救死扶伤的地方,有钱看病没钱走人。医生走后,我越想越想不通,我修炼大法做好人犯了什么罪,如今把我迫害成这样还要连累丈夫在这里,不但不能出去挣钱养家糊口,每天还要花费很多的费用,并且还一次次的想给我构陷材料罗织罪名恐吓我。真是不给人生路啊!我不能配合这种迫害行为。看着眼前不明真相的监视我的两个小特警,我告诉他们了真相,便开始绝食反迫害。
当绝食到第四天时,体重由一百多斤降八十多斤,大腿已经变成了皮包骨。当我的姐姐再一次来看我时,看着眼前身体被折磨的不成样子的我放声痛哭。当我让姐姐为我拿便盆小便时,便出的都是血。医院向当地国保队作了汇报,第二天国保队长钟民又请示了公安局长段于建,让我丈夫拿三万元的保释金、三万元的医药费才能放我回家。憨厚老实的丈夫被逼的说:我们哪有这么多的钱哪,你们还讲不讲理呀!丈夫为了给我收拾一下个人卫生,给我打来水想让我洗洗头,我洗完头正坐在床上擦头时,突然觉的心脏不舒服上不来气,憋的大声大声的叫,身体不由自主的抽搐不能说话。我被抢救过来之后,因又增加了三千多元的医药费,医院把我赶到了走廊里,我拖着虚弱的身体躺在一张小床上。直到晚上五点多,国保队长钟民给我丈夫打来电话说要给我办所谓的取保候审,看我们没钱保释金先不用交,并让我丈夫过去一趟,威胁我丈夫说人要跑了就找我丈夫要两万元钱,没钱就拘留我丈夫。
一个月之后,公安局又打来电话骚扰,让我丈夫用车把我拉到公安局,说要了解情况。为了躲避再一次的被迫害,我和丈夫被迫流离失所、四处打工为生,直到现在。我的身份证、手机、劳动教养票子直到现在被他们非法扣押。
二零一八年七二零前夕,我和丈夫在河南亲家家里做客,当地公安局又去抓捕我们,在好心人的帮助下我们顺利脱险。
长达二十年的迫害,不但给我本人精神、肉体、经济上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同时也给家人带来了无尽的痛苦。我的外甥看着我和丈夫过着漂泊不定的日子,背着我私下里给公安局的人(外甥怕我去要,不告诉送给哪个人了)送了七万元钱想了结此事。但是直到现在他们不但不返还钱,还四次抓捕我。
今天将我被迫害的事实写出来,我的心中没有半点怨恨,只是想让那些不明真相、还在继续参与迫害的人能够醒悟,不再为中共邪党卖命,在中共邪党覆灭之前作出正确的选择,让自己的生命保平安,让自己的亲人保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