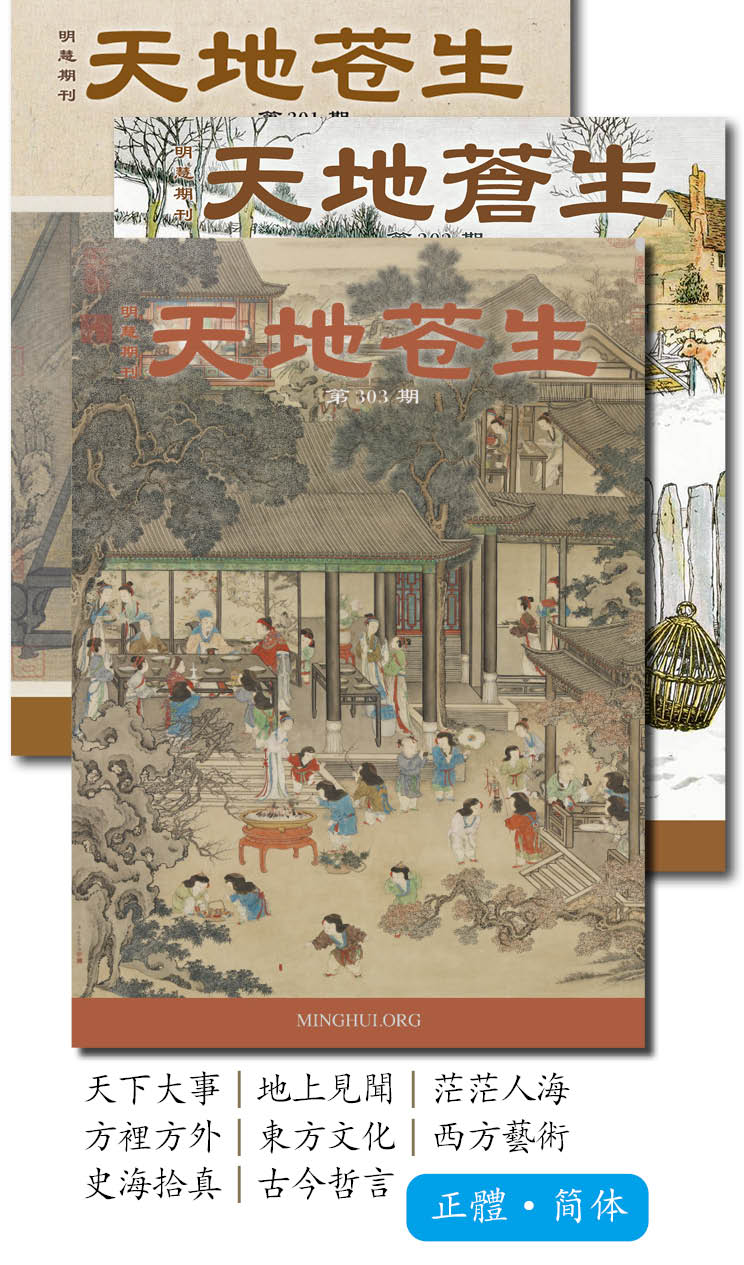云南昆明市法轮功学员肖玉霞遭迫害经历
下面是肖玉霞女士自述被迫害的经历:
我叫肖玉霞,家住昆明市官渡区五里村委会新草房村,一九九七年走入法轮大法修炼。修炼后我的静脉曲张、妇科疾病、心脏病等疾病都不治而愈,在真善忍法理的感化下,我与婆婆、姑太之间的矛盾都缓和了,而且越来越好。
合法上访被行政拘留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江泽民集团公开迫害法轮功。我觉得大法教我做好人,没有错。二零零零年四月四日早上九点,我和其他六十位法轮功学员一起到云南省委办公厅上访,反映我们修炼法轮功的真实情况。有几个法轮功学员进到信访处办公室与工作人员交流,我们就在外面等候,到中午十二点左右,根据法轮功学员家庭住址的户口所在地,各个派出所来了几辆警车,把大家分别带到各个派出所和拘留所,我被带到了官渡区行政拘留所行政拘留了十五天。
进京鸣冤被非法劳教三年
二零零零年七月二十三日,我和其他几个法轮功学员去北京,我们来到了天安门,准备在那里炼功,刚刚坐下,天安门的警察就全部围上来了,问我们是哪里的,我们回答:“云南的。”又问是法轮功吧?我们回答是。就这样警察上来拉的拉、扯的扯把我们拉上了警车,送到了北京一个专门关法轮功学员的地下室。
一间十多平方米的房子关了十八个法轮功学员。北京的警察通知我们当地派出所去接,我在那个地下室呆了三天,每顿就给一个馒头,也不给水喝。三天之后菊花派出所的警察和我们村的队长来接我,把我接回昆明后在菊花派出所关了一晚上,第二天就送到昆明市第一看守所。就我在北京地下室呆的这三天,以及警察和队长来接我的来回路费,从我和丈夫两人的年底分红中扣了一万三千元,我们每个人的年底分红是六千五百元,连同我丈夫的都被扣了。
我在昆明市第一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了四十五天。每天被强迫拣辣椒,两个人拣一大麻袋辣椒,从早上七点钟,要拣到晚上十点半左右,每天如此,指甲都拣掉了,流血了,十个手指每天晚上都辣的睡不着。吃的伙食是最差的煮苦菜和白菜,菜汤上还漂着小虫,偶尔有几片肥肉。
四十五天后我被劫持到云南省女子劳教所非法劳教三年。每天强迫劳动,
第一天,包夹就用力推我让我去干活,差点让我栽到地上。干了一会儿,张队长过来骂我,让我站在那里听着她骂,骂了一、两个小时,我都站不住了,她也骂不动了,才又叫我去干活去。我从那天起就开始整天拣盐水菌,从早上七点到下午六点,手成天泡在盐水里,手都泡肿、泡白了。而且成天就是低着头拣菌,不许抬头,抬一下头就被包夹骂。
晚上六点多干完活,其他人休息了,还要我去背所规,还要抄,要背到十一点多,持续了两个多月。两个多月后,辽宁省马三家邪悟者到女子劳教所来“转化”大法弟子,我也稀里糊涂地唯心“转化”了。
之后我还干过下地收白菜、缝十字绣等活。我在劳教所呆了八个月左右,于二零零一年四月二十五日回家。回家后,每逢遇到所谓敏感日,菊花派出所警察、村上队长就会来家里骚扰,让我不要出去。
被非法判刑五年
二零一二年二月七日,我和其他一些同修在云南省陆良县的同乐广场被绑架,当晚就把我们十四位法轮功学员关在陆良县公安局的一间大会议室,不让睡觉。之后分别把法轮功学员带到其他办公室连夜审讯。我当晚被审讯了三、四次,问我们多少人来,从哪里来的,来干什么,谁组织的等等。最后把我和吴奇慧、蒋雪梅三名法轮功学员送到医院体检身体,然后送到陆良县看守所非法关押。拘留书上给我们的罪名是“流窜作案”。
二零一二年七月三日,云南省曲靖市检察院一所谓“破坏法律实施”非法起诉我们三位法轮功学员,代理检察员是吕昕泽。起诉书最后有附项,所谓证据目录及主要证据复印件一册,但是没有给我们。我们接到起诉后才几天,七月二十七日在陆良县法院就秘密开庭,对我们三人进行非法庭审。开庭时,云南省曲靖市检察院检察员沈家斐、代理检察员吕昕泽出庭,在法庭上,审判长多次打断我的正义律师为我的辩护,甚至威胁律师,如果再为我展开做无罪辩护就把他赶出法庭。
当天早上九点多开庭,到中午十二点左右结束,一开庭,律师就要求法庭让家属进入法庭旁听,审判长不同意,说是不公开开庭,可是庭下坐了好多国保大队警察、“六一零”人员,律师就提出如果不公开开庭,那么庭下所有在场的人都必须离开,也被无理拒绝。家属都只有在庭外等候,当天小小的陆良县法院开来了好几辆特警车,还有好多便衣、警察,在法庭外对我们的亲属朋友录像,一直到开庭结束,我们又被送回看守所,家属离开后,这些人才走。
云南省曲靖市中级法院二零一二年八月十六日对我们三人都非法判刑五年。我们都要求上诉。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三十日,云南省高级法院非法维持原判。审判长姚永,代理审判员杨国强、张赵琳,书记员李静。
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的迫害
二零一三年三月一日我们三个法轮功学员一起被送到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才到监狱的第一天,就让我们脱光了衣服所谓检查身体,把我们自己的衣服收了,强迫穿劳改服。我们都被送到九监区,我的责任警是夏昆丽。换了衣服就发一个小板凳说叫我们“坐着学习”,其实就是坐小板凳体罚。才去也没有生活用品,包夹叫我写申请买生活用品,我写了几次都不合格,非要写上自己是犯了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判了多少年,所以我几次写的都不行。
九监区对法轮功学员的学习就是每天从早上六点半洗漱后就开始坐小板凳坐到晚上十点二十,十四个小时(中间给两个小时站起来活动一下)的时间就那样坐着,只有每周星期天休息不坐小凳,不准和任何人说话,不准闭眼睛,不准弯腰、驼背,要坐的直直的,除了上厕所、洗碗,其它时间连监房的门都不能出。我们所有法轮功学员一入监就被无理的以严管级对待,监狱的分级处遇是接到判决送入监狱后,根据在监狱的表现而给予的处遇,可是法轮功学员一入监就被非法严管,从最基本的生活一直到在监狱该享有的基本权利都被以“严管”的名义非法剥夺,以这些来逼迫法轮功学员“转化”、放弃信仰,只有写了“三书”才解除严管,才享有和其他犯人一样的权利。
我在九监区一个星期只给在监房里打一盆水来擦一擦身体,洗头也是在监房里,也就是和擦身上一起洗一次。洗衣服也是一周一次,在监房里洗好了,安排抬着到洗漱间去清衣服。所谓的洗澡、洗头、洗衣服一共就给两盆水,三个月才给洗一次床单被子,洗床单被子的那一次也只给那两盆水。也是洗好了抬到外面的洗漱间去清,给两桶水清,单洗衣服那一次是一桶水,洗被子那次才是两桶水。一天从早到晚上厕所的时间和次数都是被限制的,在厕所里稍微时间长一点,包夹就要骂,如果拉肚子要额外去上厕所,还要报告,得到允许才可以去。九监区的法轮功学员,每个法轮功学员关在一个监房,为了防止法轮功学员之间见面,所有的安排都是由犯人监督岗叫,叫到了才可以去上厕所、叫到了才可以去清衣服。此外,包夹随时盯着法轮功学员,不许法轮功学员和任何人讲话,就成天坐在那里,连最基本的生活、生理需求都被剥夺,还美其名曰是“学习”。
以上是身体上的迫害,除此之外,女二监还有不断的精神迫害。
女二监从二零零一年开始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以来,在九监区专门成立一个分监区“专管分监区”,分监区下设几个组,叫专管组,一个组由一、两个警察负责,每个组都有专门的一批犯人,专门包夹法轮功学员,都是些判死缓、无期徒刑的长刑犯,专门配合警察“转化”法轮功学员,这些犯人被灌输的就是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谎言,并以给奖分刺激她们“转化”法轮功学员,表现积极的就给奖分。
三个包夹为了逼我“转化”,尽其所能在生活上刁难我,精神上羞辱我,诋毁大法,诱骗我“转化”后会改变在监狱里的待遇,而所有这些都是在警察的授意下所为,我还被强迫看污蔑大法的书,邪悟者的言论,把其他人的“三书”拿来给我看,甚至还说帮我写好,让我签个名就行了。而狱警三天、两天就把我叫到心理咨询室,要么伪善的一面来欺骗,要么就恶毒咒骂,要么就吓唬、威胁,反正就是要让我“转化”,还强迫看污蔑师父、污蔑大法的录像。看录像时,专门叫我贴着电视机坐,用那种方式来逼我“转化”。就因为我不“转化”,监狱不给我家属会见,不给打电话、不给通信。二零一三年年底,警察夏昆丽骗我说监狱不给我寄信回家,她帮我私自带信出去,叫我写一封信。我就写了信,拿去给她了,她随便看了下就开始骂我,说的非常恶毒,我当时一句话也没说,她骂完了,可信却没有给我寄。我回家后问了家里人,说根本没收到什么信。
二零一四年二月份,我被关到二监区。二监区是全监区出监劳动,也不让我出监劳动,专门就安排两个犯人在监房里守着我,基本的作息时间和管理方式都和九监区差不多,只是说洗漱可以出监房去洗漱房洗漱。但是也是一周才给洗一次头、洗一次澡。我就又那样在监房里坐了一年半。后来说是监狱规定凡是有劳动能力的都必须出车间劳动,要求我必须去车间。虽然安排出车间劳动,可是专门安排两个“三人包夹”,随时盯着我,不让我跟任何人说话,我在车间上厕所时,为了不让我和其他犯人讲话,两个包夹就有一个要站在我面前盯着我。平时在车间劳动时,两个包夹也都一左一右的在我旁边,盯着我。警察也是一前一后的跟着我,在车间劳动专门把我安排到警察值班室旁边,叫我剪线头。二监区是专门制作警察的衣服裤子,包括衬衣、内衣等,劳动强度非常大,从早上七点到车间,到晚上十一、二点钟才收监回来,没有固定的休息天,所谓干完一批货就给休息个一两天左右,有时候连着干,要干一个月都没有休息。警察还对我说,下车间劳动多好,时间过的快,这是监区对你的照顾,没“转化”是不给下车间劳动的。我说:“这是变相迫害!”
二零一五年五月份,主管狱警何新楠、教育科狱警曹蕊、林晓雯(已经辞职),还有从外面叫来的一个什么邓教授,四个人成立一个组,扬言非要把我“转化”了。星期六、星期天他们休息,让我去车间,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我关在监房里,这四个人轮番轰炸我,逼我“转化”。这期间,九监区的警察李国英也来了四次,跟我套近乎,诱惑我“转化”。这几个人从各个方面,或唠家常、或吓唬、或威胁、或伪善,拿水果来给我吃,反正就是要我“转化”,整整四十五天。期间还把我女儿也给骗来了,女儿见到我,当着警察的面也勉强的说了我几句,我回给她说:“你怎么被他们给搞成这样?你妈是个什么人,你不知道吗?”女儿也就不说话了。
二零一六年年中,二监区把我和其他的犯人叫到办公室里,又让我们脱光了衣服检查,叫“裸清”,我说这是天大的侮辱。当时二监区非法关押着我、杨木花、黄喜兰、蒋雪梅我们四个法轮功学员,黄喜兰也被这样裸清了。分批清,她是第一批清,我是第二批。我们四个法轮功学员,也是不让我们互相讲话,不让碰面。
我在九监区只接见了一次,监狱安排女儿、“六一零”和村委会的人来了,利用所谓的亲情帮教想让我“转化”。后来到了二监区,我丈夫和女儿来接见过一次,后来就不给我丈夫见了,只让我女儿见我,却借此来诋毁我说我们不要亲人不要家。
二零一七年二月六日,我结束五年冤狱,从监狱回家。回家后,菊花派出所的片警来家里骚扰了三、四次。
如今回想被迫害的这些年,我想,真正被迫害的是那些被中共谎言欺骗了的世人,因为被欺骗了,才追随中共在无知中作恶。随着法轮大法真相广传,我相信法轮大法真相大白于天下的那一天已经越来越近,希望迷中的世人啊,快快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