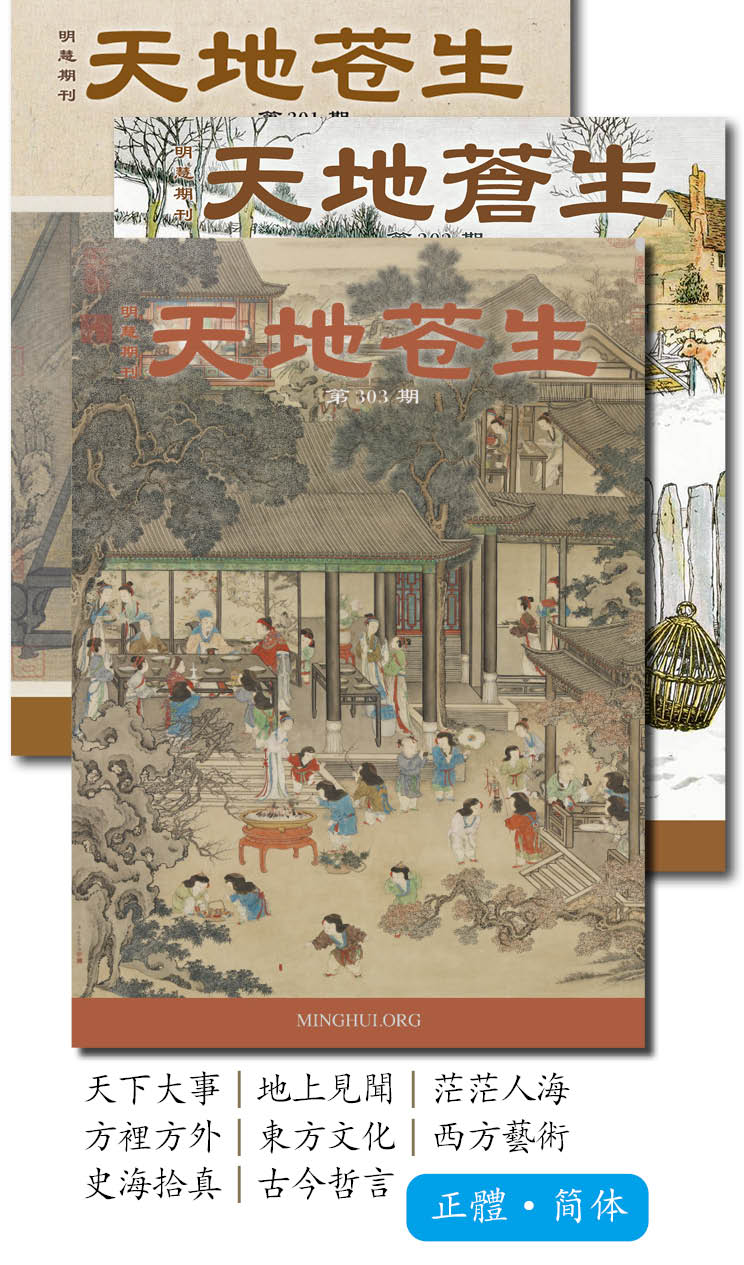兰州法轮功学员李秀兰叙述遭迫害经历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后,邪党铺天盖地对大法对师父的诽谤,让我非常难过。我先后三次进京上访,要求还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为大法说公道话。我三次都被警察绑架,被非法关在兰州市城关区桃树坪拘留所。回到家中也不得安宁,当地派出所和我的工作单位经常派人到家里来骚扰,逼我写放弃信仰的保证,后来又要送我到洗脑班迫害,我没有配合他们,被迫流离失所。二零零零年至二零零八年期间我被迫搬了十次家。
二零零八年四月十三日,我取真相资料时被兰州市城关分局的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兰州市第一看守所八个月。二零零八年九月二十七日,兰州市城关法院对我和金俊梅、岳丁香等法轮功学员非法开庭,当场没有宣判结果。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十日,兰州市城关法院人员金济勇到兰州市第一看守所非法宣判,我被非法判刑七年。因为第一看守所生活条件太差吃不饱饭,卫生条件也很差,我得了疥疮。
二零零九年元月我被劫持到甘肃省女子监狱,在那里受尽了种种欺侮。那里根本没把我当老人对待。强行“转化”,不让我睡觉、不让喝水、不让上厕所、不让说话。经常罚站、罚蹲、罚干活,拳打脚踢,扇耳光、往脸上吐痰、抓起头发往墙上撞等等都是家常便饭。
包夹我的第一个人是经济犯辛丽荣。因为我年纪大,不会干活,经常挨打,有一次她用拳头将我的胸部打的都半个月了出气还疼,睡觉疼得翻不了身。还有一次辛丽荣踢我的腿,膝盖都被踢肿了鼓起一个大包,很多天无法走路也蹲不下来。有一段时间因没按她们的要求写思想汇报,她就打我的脸,眼睛也打肿了,肿到睁不开。我对她说:你把我打瞎我就不用写思想汇报了。她才打得慢些了。晚上写不完思想汇报不让睡觉,早上不让洗脸,我要偷偷洗了,她们就逼着我喝洗脸水,衣服也不让洗,被子叠的不符合她们的要求就逼我抱着被子到大厅去“学习”(一遍又一遍打被子,踩被子,折腾你)。平时辛丽荣吃不完的饭菜就倒给我,逼着我吃。星期天休息时她躺在床上,让我把米饭弄碎帮她美容。
二零一零年,犯人吴金凤包夹我。她经常敲诈我,让我给她买东西吃。我的用品食物她随便拿,我连一句话都不能说。我没用的没穿的了她还说是我弄丢的。就算这样她还是没完没了找麻烦。经常不让我洗澡。以前那些包夹犯人打人动作大动静也大,她是不哼不哈掐我的嘴、脸、腿、胳膊,用脚踩我的脚。还经常把我拉到厕所里打。
二零一一年,犯人支英开始包夹我,表面看她对我还挺好,背地里狠命整我,我背不下“弟子规”时,写思想汇报不符合她们要求时。就拿铁尺子打我的手。还逼着我脱掉自己的鞋子打自己的嘴。也是把我的东西当成她的一样用。每次去小卖部买东西由她选择,我掏钱。只要有好吃的都要给她买上。当狱警知道了这些事后,她就打我,有一次她报复我罚站几个小时,我都站晕了,直接栽倒在地上,她们还说我是装的。
 中共酷刑示意图:殴打、撞头 |
第四个包夹犯人叫陈丽,二十出头的年纪,我成了她的出气筒,她几乎天天打我。扇嘴巴子、用脚使劲踹、揪着头发往墙上撞都是经常事。有一次被陈丽抓住头发,将头塞到了桌子的抽屉里。大冬天不让我用热水,还经常逼着我吃药。狱警逼着我写思想汇报,不符合她们要求就写到深夜,陈丽要睡觉,我写字的纸一响她就打我,写不完她也打我,每天都在打。打完还让我给她洗衣服,我的衣服泡在水里不让洗。还经常不让喝水不让上厕所。我一个六十多岁能当她奶奶的人,她能把我打到无法走路。她经常揪着我的头发往墙上撞,致使我的头一直是木的。我自己不记得了,可是别人说有一段时间我自说自笑,精神都不对了。
监狱里是有摄像头的,陈丽肆无忌惮的所作所为谁都看见了,狱警能看不见吗?!能不知道吗?!要是有人管,谁敢无所顾忌,那是监狱,她是真正犯了法的呀,她敢这样做是狱警在放纵她,她们打人,狱警不管。看实在说不过去了,狱警怕出人命,怕担责任,怕牵连到自己,才出来做作秀装好人,好象还主持了公道,去收拾穷凶极恶之徒。比如有一次在大厅“学习”时我没有通过陈丽向发药的犯人要了一个小药瓶准备装盐,陈丽为此又对我大打出手。让狱警丁海燕看见了,把陈丽叫到办公室打了两耳光。陈丽回来后气急败坏的说:“我长这么大还没被别人打过脸,今天打了我两耳光,脸都打肿了。其实都是队长让我们折磨你们的。”
被非法关押在甘肃女子监狱的六年里,我身心备受摧残,体重从一百三十斤降到九十斤,身上经常被打的青一块紫一块,就没好过。精神上更受到极大的摧残,真的生不如死,不堪回首,那真是地狱般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