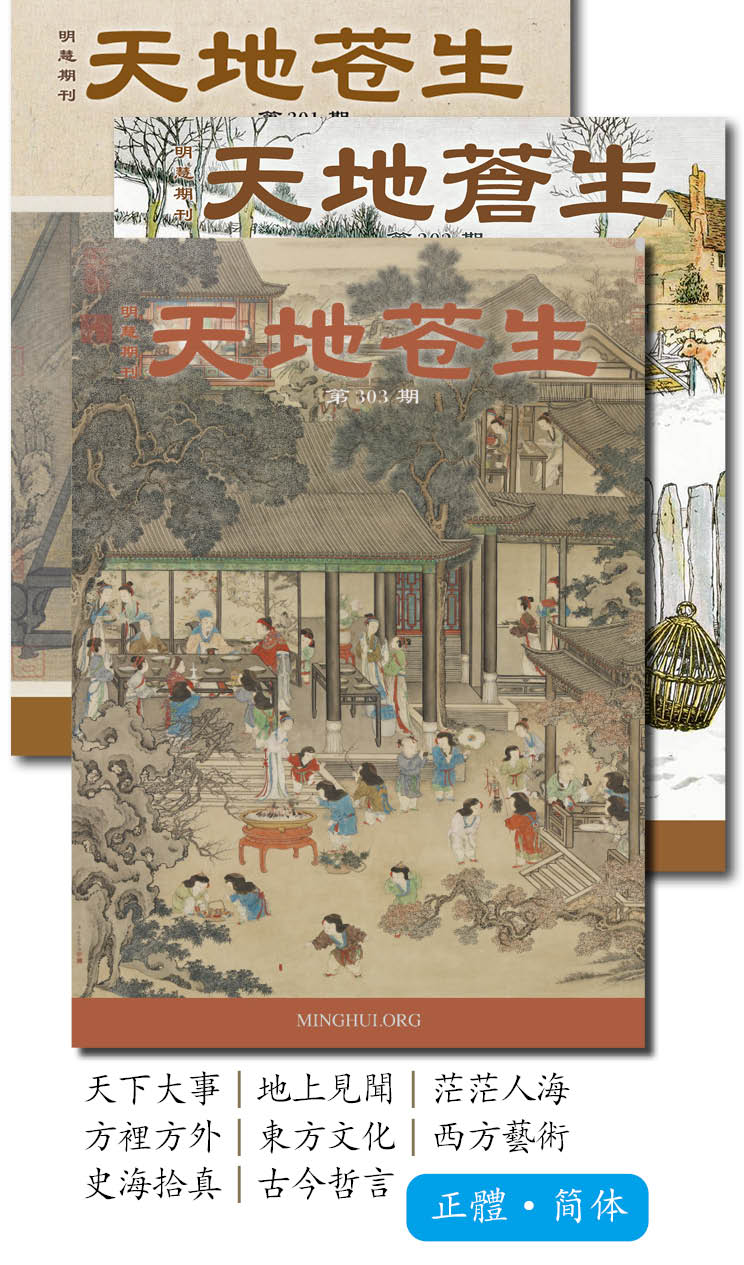退休教师:我在自己的国家居无定所、有冤难伸
 刘秀春 |
我叫刘秀春,今年七十二岁,是河北省兴隆县一中退休教师。老伴叫陈同庆,七十三岁,曾在天津蓟县几个中学当过教师,已故。我俩因炼法轮功在二零零二年一月分别被非法判刑五年和八年。
得大法 绝路逢生
修炼法轮大法前,我俩都百病缠身。我最严重的是心脏衰竭,一犯病就休克,还有声带小结。犯病时不能说话,还憋气,憋起来难受打滚,需做手术,但手术后有八成可能变成哑巴。
老伴是哮喘,天冷也喘,天热也喘,犯病时一天天的在地上撅着。另一种是小肠疝气,在小腹长出一个碗大的包。一犯病就大汗淋漓,两腿无力走路。他外出经常是被人用板车推回家。那时成天就是吃药、打针、输液,挂急诊,住院,到处找偏方。
我俩每犯病就是在生死线上挣扎。不去看病不行,可病越治越恶化。我总和老伴说:是不是咱俩活到头了?他说:要不是为了儿女,我早就不想熬下去了。当时家里根本就不象过家的。看着我们痛苦的样子,儿女们个个愁眉苦脸,眼泪汪汪的。
一九九八年一月,老伴从蓟县得到一本《转法轮》。他看了一遍,我也看了一遍。看完以后,我俩都说出同样的话:“这书真好!”当时到处都有炼法轮功的,于是我俩决定到公园参加集体炼功。学法炼功不到一个月,奇迹出现了,我和老伴全身的病不翼而飞,我的声带小结消失了,老伴小腹碗大的包也消失了。儿女看到父母的变化,个个喜出望外,从此家里有了笑声,有了欢乐的气氛。大儿子逢人就说:我爸妈炼法轮功病都炼好了,都能干活了,也能给我们做饭了,我家也过上幸福生活了。法轮大法真好!
大法的超常、神奇,师父的伟大慈悲、佛恩浩荡,使我与老伴的修炼之心坚如磐石。
匪警 抢钱夺财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江氏流氓集团利用中共邪党疯狂迫害法轮功。兴隆县政保科警察大肆迫害法轮功学员:抓人、打人、拘留、劳教、判刑、抄家、罚款,一片红色恐怖。当时的政保科大队长朱俊春勒索被抓的法轮功学员大肆勒索钱财,少则五千元、多则六万。以下是我所经历的和亲眼见到的:
1) 我第一次被抓,在看守所被关押一个月,朱俊春向我儿子勒索五千元。
2) 老伴上北京证实大法被殴打,后被送回兴隆,在看守所被关押一个月,朱俊春向我儿子勒索五千元。
3) 一位庞姓法轮功学员因讲真相被朱俊春罚款八千元。
4) 朱俊春一天突然闯进刘姓法轮功学员家里抄家,抄到一本《转法轮》。以此为由,派人到刘姓法轮功学员打工的饭店绑架了她。朱俊春向她开价两万,她交了一万,还不放人,家人又买了一份厚礼给他,他才放人。
5) 朱俊春一天闯入谭姓法轮功学员家里,搬走电脑,还勒索一万元,不交钱就开除他两个儿子的公职。两个儿子吓坏了,急忙每人拿出五千元给了朱俊春。有一次朱俊春对张姓法轮功学员说,老谭太老了,我不抓他了,我就经常不断的来一次。果然他又有两次突然闯入老谭家,勒索了两万元。
6) 一次大搜捕中,当地一当医生的法轮功学员被抓。朱俊春向他家勒索六万元,交不上就判刑五年,家人只好交上六万元。
7) 一法轮功学员上北京探望在北京打工的老伴,在被警方得知她炼法轮功后,被遣送回兴隆县,政保科把她打个半死,还勒索了五千元。
8) 我一邻居法轮功学员发真相资料被抓,罚一万,他家只能拿出一千,又找我借了两千。政保科警察嫌钱少,将他劳教三年。
9) 我家五次被抄,政保科想拿什么就拿什么。新买的录放机还没用就被抄走了。一次闯入我家,见新换了一台东芝电视机,就给抄走了。最后一次闯入我家,见没啥可拿的,就把手电筒拿走了。
警察当场私分我儿子的学费
二零零二年,因为当时大儿子和女儿都已成家,小儿子在湖南上大学。为了躲避当地政保科的迫害,我和老伴决定离家出走。我们把在兴隆一中宿舍区的房子卖掉,带着两万元房款来到天津蓟县租房住下。一次,当地法轮功学员说:蓟县马伸桥派出所抓了二十位法轮功学员。十九人被罚,一人两千;有一人没罚,是因为这位法轮功学员被打死了。我们意识到当地迫害也很严重。
一次去集市遇到一位亲戚,他告诉我蓟县当地警察正打听我俩的住处。我俩赶快回到租住的地方,把制作真相的设备耗材转移,然后离开。过了十天,我俩回到租住的地方。一进院子,就上来一个警察打了我一记耳光,怒吼:怎么走这么长时间?这时一群警察围上来,一个孙姓的大队长(戴眼镜)抢走老伴手中的皮包。老伴高声说:里面有二千三百元钱,那是我儿子大三一年的生活费,你们不能没收呀?可是这帮恶警根本不理睬,当场就把这二千三百元钱每人二百元分了。
房东告诉我们,他们在这蹲坑已有几天了,把我家的一盆鸡蛋煮成茶叶蛋吃了,还把我们在山上采的蘑菇也拿走了。
我俩被押到蓟县分局政保科审了两天两夜,老伴没吃、没喝戴着手铐站了两天两夜。我在另一个房间坐在地上两天两夜。
老伴被判刑八年
随后,我们被关押在蓟县看守所长达十个月的时间。在看守所里面,早晚只给两个窝头,一碗清水咸汤。窝头不搪时候,过一会就饿。中午老伴找警察要吃的,警察也不给。其他有钱的犯人可花钱购买食物。老伴长期挨饿,后来他发现有的人把吃不了的窝头掰碎了扔在厕所的垃圾桶里。老伴就在每次上厕所时在垃圾桶里快速的翻找,然后捡起里面的窝头吃掉。因为上厕所限时,有时手上粘上大便都来不及冲洗就吃了。就这样老伴吃了十个月的垃圾饭,人瘦了二十斤。
老伴被判刑八年,关押在天津港北监狱,那里非常邪恶,对法轮功学员施行酷刑。多数都被迫违心的“转化”了,我老伴也经历了各种迫害。例如在三九严寒,狱警把他关进一间冰冷的房间,脱光棉衣棉裤,把前后窗户敞开,寒风刺骨,再往他身上泼凉水,一天天的冻他。在狱警的指使下,有时包夹用脚后跟猛跺他的脚趾头,有时跺出血,有时剁掉指甲盖。一边跺还一边吼叫:你怎么还不“转化”,急死我了!?一年后小儿子探监,一看到他不禁失声痛哭:爸爸,你怎么变成这样了?我老伴从一个健壮挺拔的男子汉变成一个弯腰驼背的干瘪小老头。
老伴不畏强暴、正念正行,随时都正法,大会小会他都站出来证实大法,揭露邪恶。法轮功学员们都佩服他,连恶警都尊敬他。老伴的正念正行影响着监狱的“转化”率。一天老伴突然象得了脑血栓(其实是师父演化的),被送到医院,监狱马上批保外就医。在师父的加持下,老伴两年闯出黑窝。
出来之后,老伴回到兴隆县。房子已卖掉,大儿子在精神病院,退休金被扣,身无分文。当时兴隆县迫害形势还很严重,老伴考虑到自己刚刚从监狱出来,不能给其他法轮功学员带来安全问题,就孤身一人流浪街头。一开始有两个拾垃圾的看他没饭吃,就时不时的给他一些食物和衣物。后来老伴自己讨饭吃。老伴找到一间废弃的地下室住下,地下室里没有床,什么都没有,老伴就睡在地上。到了冬天,地下室非常寒冷,饥寒交迫,老伴又辗转来到蓟县,找到昔日的法轮功学员,吃饭有了着落,又开始做三件事。当时蓟县资料点少,他就在山坡上两间废弃的房子里和其他法轮功学员制作真相资料。这个资料点很大,几乎蓟县全部的资料都从这里取。过了一段时间被警方查获,所有的耗材、机器被抄走,损失很大。老伴又一次被绑架。恶警们日夜审讯他,无论恶警怎么问,他只回答:不告诉你。恶警威胁他:这次必须配合,问啥说啥,不然上次判八年,这次判十八年。老伴不动心,心想:一切由师父说了算。在师父的保护下,在二十天后,老伴又正念闯出黑窝。
天津女监:刑罚、饥饿、奴工……
二零零二年,我被非法判刑五年,关在四监区。恶人榜上的李红当时就是第四监区的监区长。她迫害法轮功学员招数损,花样多,杀人不见血。第一天就叫我坐小凳子,姿势叫“三挺一蹬”,两脚两腿并紧,两手平放在大腿上,腰挺直,全身一动不动,象木桩一样,固定在凳子上。一般人坐上三十分钟就受不了,李红让我一坐就是十五个小时(早六点-晚九点)。遇到心狠的包夹,动一动包夹就吼叫着拳打脚踢;遇到心善的包夹,李红就换掉。不长时间臀部就长疮,流血流脓,坐在小凳子上痛的如同坐在刀尖上。伤口常年不愈合,腿变得不会走路。星期日和节假日的中午,全屋人都休息,只有我一个人三挺一蹬的坐在小凳子上。一位张姓法轮功学员就是被这种阴损的酷刑折磨至双腿残废不能走路。一天我在走廊里听到李红对包夹倪亚萍说:你对刘秀春怎么做都不过分!
 长时间罚坐小凳子 |
本来监狱里的早饭和晚饭是馒头和咸菜,午饭是饭菜。四监区长李红采取卑鄙手段,把早饭和晚饭的咸菜给掐了,只有馒头就白开水,造成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常年挨饿。不吃咸菜,肚子会饿的很快,因为饥饿我一宿一宿睡不着觉。
不久又来了一个叫吴春环的恶警,配合李红变本加厉的迫害法轮功学员。她限制吃饭时间只有两分钟。吃午饭时,包夹倪亚萍手里拿着一个小闹钟,二分钟一过,立刻从我手里抢过饭碗,将剩下的饭菜倒进脏水桶。吃早晚饭时,也是两分钟一过,抢过馒头扔进垃圾筐。每天三次都是这样,同监室的其他犯人都不忍看这一幕,有的偷偷流泪。我的头发变白了,还一把一把的掉,掉成秃顶。牙也一块一块的掉,一个一个的掉,五年中我掉了十五颗牙。除了饮食上的迫害,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还不能洗澡。偶尔洗一次连脱衣带冲洗只有五分钟,脱光衣服刚一冲就到点了。每天洗漱二分钟,常常只洗了一只脚就到点了,另一只脚就不让洗了。
让我最痛苦的还不是四监区对我身体的摧残,而是精神上的迫害。李红安排每天四五个人(有“犹大”、刑事犯和包夹)对我进行“转化”。她们在李红等恶警的唆使下,在会减刑的蛊惑下,就像开批斗会一样,对师父和大法进行污蔑和诋毁。我忍不住斥责他们,遭到更严重的迫害,白天批斗我,晚上屋里两个大灯不关,照的全屋犯人都休息不好,有的犯人还起来要打我。
天津女子监狱对我长期精神上的高压迫害使得我精神达到崩溃的边缘,我违心的“转化”了。后来我不坐小凳子了,开始到车间干活。开始是搓绳,给缝制出口篮球的提供纫绳。后来是制作出口国外殡仪馆的假花,将加工处理后染上颜料的玉米叶折叠成各种样式大小的花朵造型。因为这种处理过的玉米叶含剧毒,没有一家企业会接这种活,可天津女子监狱常年做,到现在还在做。有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一干活就全身浮肿,有人手烂,有人呕吐,所有人的手一层层的脱皮,头发变黄变干变脆。完不成生产指标就罚站、擦厕所、擦地板、不许购物。回想起那漫长的五年,真是度日如年。
大儿子被迫害吓到精神失常
大儿子高考落榜后参军,复员后在单位开车。爸妈修炼法轮功,他由衷的高兴,再也不会因爸妈随时犯病存在生命危险而担惊受怕了,再也不用和医院打交道了。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中共邪党开始迫害法轮功,邪恶的诬蔑铺天盖地而来,大儿子越看越害怕,他不明白只是炼功祛病健身的爸妈怎么一下子成了政府的敌人、中共打击的对象?特别是爸妈一次一次被抓、被罚款,又经历了五次抄家,他的精神受到严重刺激,得了精神病,去医院也治不好。特别是在二零零二年我俩双双被判重刑,大儿子就彻底疯了,工作干不了,大雪天光着身子在大街上跑。单位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到现在已经整整十年了。
妻子也和他离婚。二零零七年我出狱后,和老伴买了礼物到儿媳家想看看孙子。儿媳没给开门,也不让见孙子。我们去了几次都没开门。我虽然很失望,但我不怨儿媳,是江氏流氓集团利用中共邪党害的我们家妻离子散。
老伴离世那天,大儿子才从精神病院回家。
小儿子在饥饿中毕业
小儿子上大三的两千三百元生活费被蓟县政保科的恶警们给抢走了。他向亲戚们借,可谁都不给他,怕受连累;只有表姐借给他七百元,还说是孩子的压岁钱,是孩子借给的。可这也不够呀。正为难时,一位法轮功学员送来三千五百元钱,大三的生活费才有了着落。
到了大四,小儿子就只好向同学借,借到就有饭吃,借不到就饿着,吃上顿没下顿,有时一天天不吃饭,大四这一年靠着同学的接济总算勉强过来了。大学毕业了,品学兼优的小儿子因交不起两年的学费,也不敢向学校领导讲明原因,学校不给发毕业证。没有毕业证找不到工作,小儿子就在湖南街头流浪。爸妈坐牢,哥哥疯了,自己又找不到工作,家庭的变故、残酷的现实,年纪尚轻的小儿子走投无路,好几次想跳江寻死。但是想到爸妈的期待,最后还是打消了念头。
后来小儿子终于找到一份月薪七百元的工作,干了两年凑齐了学费,才拿到本科毕业证。小儿子后来在深圳一家公司工作,开始月薪只一千元。在试用期后,因为表现优秀老板一下子把月薪涨到五千元,老板说从没有遇到象你这么好的员工。可就在去年,小儿子在网上发帖维权,被深圳警方抓捕,后被遣送回兴隆。老板不想失去这么好的员工向警方求情,却遭到警察的威胁:再雇用他就封你公司。
被截断退休金 六旬老妪被迫打工
我出狱已经七年了,兴隆县各级政府官员执行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的“从经济上截断”的政策,一直扣着我俩的退休金不发。二零零七年,我回到兴隆。老伴在这租了一间半农民废弃的旧房子。我俩过的很清贫,两天才熬一锅粥或一锅汤,一捆菠菜吃上半个月,法轮功学员们时不时送来米面和油接济我俩。我一次次到学校、文教局、街道、公安政保科、县委索要退休金,可是他们无视两个老人的极度贫困,互相推诿。教委的人说:你去找抓你的人,让他们出个证明:抓错你了,我们就把退休金发给你。
我从十九岁在中学教书,有三十八年的教龄。我除了教主科,还教音乐。我的学生无计其数,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有的学生听说我出狱了,纷纷来看我,哪个学生来了都与我抱头痛哭。他们都有心帮助我讨回退休金,但谁都做不到。我们没有经济来源,我满口牙在天津女子监狱里掉了十五颗。出狱后为了挣钱镶牙,六十六岁的我不得不外出打工,日夜伺候一个植物人老人。
大监狱
兴隆县各级政府不仅断了我的口粮,还画地为牢,限制人身自由。一到这个敏感日、那个敏感日,邪党开这个会、那个会,就来骚扰或逼我们去谈话。长期监视我,我一外出就被跟踪。我在天津女子监狱苦熬过五年,没想到又进入兴隆县各级政府制造的大监狱。
两年前老伴离世,女儿接我到她家生活。女儿没工作,女婿挣钱少,还供孩子上学。女婿对我很好,常安慰我:您没啥挑费,不就是吃饭吗,我们养活的了您。可是我心里过意不去,不想给他们添麻烦。七十岁那年我找到一个小饭铺打工,只管吃饭没有工资,我也干了。
今年四月份,天津的朋友明白我心里的苦衷,让我来天津住一段时间,散散心,也给女儿家减轻点负担。可是在天津刚住下,兴隆县公安局发现我失踪,对我女儿谎称我在天津出事了,采用欺骗手段得到我在天津的住处,派了一帮警察过来,在天津寻找了三天又将我押回兴隆。
我已过古稀之年,只因为坚持信仰、坚持修炼真善忍,被中共邪党迫害的居无定所,在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家乡,却没有说理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