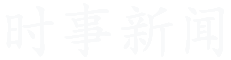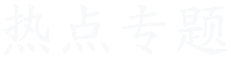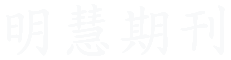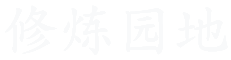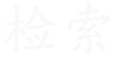辽宁省女子监狱的奴工血泪
一、入监与下队
入监队
新入监的在押人员,都要先被关在入监队一个月。在入监队,平日里要拼命地干活为监狱挣钱,星期日背监规。在入监队,新来的在押人员如果账上有钱,要在那里买生活用品,由代管犯人给配买,东西拿来了,一般五百元左右,没有明细,谁也不知道哪样商品卖多少钱。
除了发一套劳改服,一双鞋,其它一切都是自己消费。劳改服也不一定合身,还不一定是新的,监狱会把出监人员的劳改服强制收回(不交回就要扣钱)然后发给新来的在押人员。被褥就完全没有。
而按照狱务公开手册上的规定:统一配发被褥。
“下队”
在押人员从入监队被转到各个大队、各小队叫“下队”。首先搜查从入监队和看守所带来的日用品,认为不合格的就扔掉。按照规定,应该把这些物品返给家属,但狱警嫌麻烦,都给扔了,不管是多么贵重的衣物。
床上除了木板什么也没有,你自己需要买被褥来做一个很厚的褥子,还要买被型,被型就是叠的方方正正的被子,是在白天摆放在床上给人看的,就象军队的那种。这些加在一起差不多要六、七百元钱,当然你也可以买旧的,就是出监人员走后留下的,对于在押人员的最后剥夺就是在她出监后留下的东西,她们不说跟你要,但是她们不让你给人,又带不走,怎么办?就只能给所在的小队了。管事犯人把它们收取去然后卖给新来的在押人员,把钱存在狱警那作为小队的经费由狱警支配。还有劳改睡衣,冬天的、春秋的、夏天的,必须买,加一块,还得二百二十元左右(本应该配发),还有整理箱也得买,八十元左右,还有皮箱,一百八十元,都是质量最差的那种,这些东西如果是全新的,加起来一千一百元左右。
“捐”与 摊派
监舍里有电视,晾衣房里有洗衣机,还有衣服挂,但是,这些东西都不是监狱提供的。是在押人员的钱买的,监狱里管这个叫“捐”。
洗碗用的洗洁精,打扫用的洗衣粉,新年救济贫困的采买钱,干活用的拖布,铁夹子,车间用的电线,插排,小队打饭用的饭桶,监舍坐着的小凳子,几乎无一不捐,而且不得不捐,干活不给必需的工具,可是你得把活干好,怎么办,让家里人买吧,小队大队的捐款捐物,说是自愿,可是若是不捐狱警就找麻烦,谁敢不捐?
月饼、苹果、梨……每一年都有这样的摊派,在押人员,但凡账上还有钱的就得买,不买不行,还不是论斤摊派,是论箱,狱长杨莉,除了给她的下属进烂梨吃回扣,还高价摊派给在押人员食品。仅一项,她一年起码赚五十万。
二、狱中奴工血泪
危险的奴工劳作环境
服装加工车间的现场灰飞尘飘,最严重的时候,裁剪工、机台工的脸都被飘飞的布屑染成了布的颜色。可是,就这样的劳动现场几乎没发过任何劳动保护用品。在押人员想自己买,但有时候还不一定有卖的。后来,在一次检查的时候,七监区就给每个人发了一个一次性的口罩,让在押人员在检查人员来车间的时候戴上,过后,管事犯人下来回收口罩,把口罩一个挨一个的摞在一起,说是下回再用的,几乎所有的人都怒了,一次性的,往嘴上戴的东西,用过之后下回还用,下回戴的都不知道是谁戴过的,都不知道有没有传染病,后来有法轮功学员找了狱警,由于民怨太大,这事才不了了之。
裁剪工是一个比较辛苦而又有危险的工种,她们使用的工具是电剪子,工作时稍一走神就可能切了手指,一天几乎十二个小时都要全神贯注,人很难每天做到,所以,没有没受过伤的。电剪子的刀片一挨上手指,血一下子就飞溅出来,不太重的伤在车间包扎一下就继续干活,重的,那就手指头都切断了。后来给裁剪工发了劳动保护用品,铁手套,据说一只三百多元钱,对于手的保护在一定程度上起了一定的作用,以大家对这帮狱警的了解,花钱买铁手套绝非出于对在押人员的爱护,因为在押人员是狱方获取利益的工具,工具坏了是会影响挣钱的,所以就对工具做了一定的保护。听说有个监区监区长为了省钱给她们监区的裁剪工买了只有两个手指的铁手套,结果,一个裁剪工在一次作业中就把自己的另外三个手指头切断了。
超负荷的劳作时间
按照法律规定,监狱劳工执行八小时劳作制和节假日休息制度,日加班加点,应当安排补休或给予加班报酬。然而这一规定对于监狱来说就是一纸空文。
辽宁女监规定奴工劳作时间是早上七点到晚上七点,星期日休息。这个规定本身就违背了《监狱法》,但连监狱自己的这个规定,狱方都不执行,几乎辽宁女监的所有监区都是早出晚收。
狱警郑春艳,二零一一年被调到七监区任生产科长,七监区的出工时间就越来越早,收工时间越来越晚,有很多时候六点就出工了,而收工的时间有时是九点以后。而星期日被迫加班更是家常便饭。
郑春艳以压榨在押人员来讨好效忠上一级的张秀丽,而张秀丽、张小兵之流又以同样的方式去讨好效忠再上一层主子监狱长杨莉。她们以装修监舍为借口,以打扫车间为名义,占用在押人员的周日休息时间,榨取更多的利益。一年里,几乎被她们剥夺了所有的周日休息时间的一半。当法轮功学员问及此事时,狱警却说:“她们都是自愿的。”
一位法轮功学员对此向分监区长徐小明提出异议,徐小明百般抵赖,让拿出证据,法轮功学员说:好,我给你做记录。徐小明就在白天到监舍把这位法轮功学员做记录的笔记本偷走了,并同狱警科长刘胜男对这位法轮功学员进行百般刁难与迫害。
每天早出晚收,去掉匆忙的如厕吃饭时间,一天最低工作时间是十一个小时五十分,就算周日正常休息,那么六天的工作时间是71个小时,是法定工作时间的1.775倍,要算上晚上往回带活,星期天的所谓加班,就可能是法定工作时间的两倍还要多。狱警的工作时间是早上八点半到班,下午三点半下班,中午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一天六个小时工作时间。不要说监狱就那样,如果那么理所当然,郑春艳也就没必要在有人检查的时候下通知:如果有人问到工作时间,就说是一天八小时工作。七监区的科长刘舒被一法轮功学员问到此事时,竟然无耻地说:“现在不是讲奉献吗?”
狱警还公然违反监狱规定,要求在押人员每天收工都要带活到监舍里继续干,剪子也带回去了,也不怕有人自杀了,也可以在十点之后睡觉了(监狱规定十点必需睡觉)。在监控安装之后,就要在押人员把活带在监控看不到的地方干。
除了生产,各个监区的狱警队长还大量占用在押人员的休息时间排练为狱方歌功颂德的节目,早上、晚上周日,在押人员在痛苦中表演着“幸福”“感恩”。
难以逾越的定额
对于在押人员的每天工作量的定额,以前的狱务公开手册中有这样一个标准,就是在押人员的每日产值按照平均产值定量,这个规定看起来似乎合理,其实细想一下就会看出问题了,每个人的能力不一样,就算再怎么拼命也一定会有干的多的,干的少的,按照平均产值定量肯定有低于产值完不成的,这种低于产值的人与个人的客观身体条件有关,不是主观思想可以决定克服的了的,所以,这个规定就是流氓无赖式的。而实际的对于产值的规定要求,狱方还不是用平均值去定量,而是按照干活快的去定量,那么按照这种规定方式,大多数人是完不成定额数的,那就惩罚,以违法犯罪的方式惩罚:扣掉细粮,罚蹲、罚站、罚撅着、封闭食品箱,甚至撤掉床上的褥子罚睡床板等等。
盘剥与奴工产品
在一次监区的广播中,七监区生产科长郑春艳强调了一个门槛标准,就是监狱给了一个门槛标准,达到门槛标准的监区,在押人员可以拿到平均每人每月三十六元的劳动报酬,超过这个门槛标准百分之二十的监区则可以拿到平均每人每月三十七元的劳动报酬,超过门槛标准百分之四十的监区可以拿到平均每人每月三十八元的劳动报酬,但是,郑春艳自始至终都没说这个门槛标准是多少。这个门槛标准是多少没说,依据什么定的也没说。她只说:“目前,我们拿到的劳动报酬是三十八元,全狱最高的。”这并不是说在押人员被榨取的利益仅仅超过门槛标准的百分之四十,因为这个三十八元是个封顶的报酬。狱警对利益无止境的追求,在押人员总有干不完的活。
七监区目前在押人员近五百人,监区的奴工产品有:百家好、BANG BANG(南韩品牌)、ABC、森马,这类知名品牌服装都有大量加工,每年的纯利润超过三千万元,就是说,每年从每个在押人员身上榨取的利益超过六万元,这是在除去一切费用之后,包括了在押人员的吃穿住行。这六万元的数字还只是一个保守数字。
六万元在外面能很好的养活一个三口之家。但是在押人员在监狱里却养活不了自己!狱方还说是国家拨款养活在押人员,那么这些在押人员的钱哪去了,都养活谁了?
二零零五年,在押人员小燕(化名)在车间的机台操作中伤了手指,到监狱外面的医院就诊,加上回来后在监狱医院的所有花费,小燕欠了监狱两千左右的债务,小燕无力偿还,只好用每年的一点微薄的奴工报酬(当时每月只有七元五角钱)一点点的偿还,家里人寄来的钱被直接扣掉,她儿子寄来自己二百元奖学金,希望给母亲改善一下生活,也被狱方全部扣掉。两千元的债务,直到二零一二年才算还完。
只要没死就得干活
七监区一在押人员感到胸口难受,请求狱警带她去监狱医院看病,狱警说活忙,过两天吧。过了几天,人不行了,才送医院,还没到医院,人就死了。一监区一个在押人员到了监狱医院,坐在走廊的椅子上等看病,说了一句“我好累”,就死了。
法轮功学员孙丽被迫害的得了非常严重的心脏病,走路快了都会受不了。刘晓彦把最邪恶的在押人员安排在孙丽身边监视她的一切行动,孙丽天天被她们叫骂着,心脏病更加严重。一次孙丽的心脏病又发作了,去了医院,回来的时候就实在走不了路,有在押人员让孙丽坐上她推去的手推车上,被狱警刘晓彦阻止:“让她自己走!”后来,孙丽外诊,回来之后要用一种仪器二十四小时测量心脏,这种测量要求在正常生活状态下进行,包括正常的生产劳动,刘晓彦却把孙丽带到监狱医院,强行要求医生让孙丽住一天院,即使这样,检测出来的结果还是很严重的,孙丽的最高心律与最低心律相差八十左右,刘晓彦还是那句话:“啥事没有,放心干活吧。”
法轮功学员石葳被医院诊断为腰肌劳损——实际是腰椎间盘突出,刘晓彦还是说没事。
English Version: http://en.minghui.org/html/articles/2014/2/27/14562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