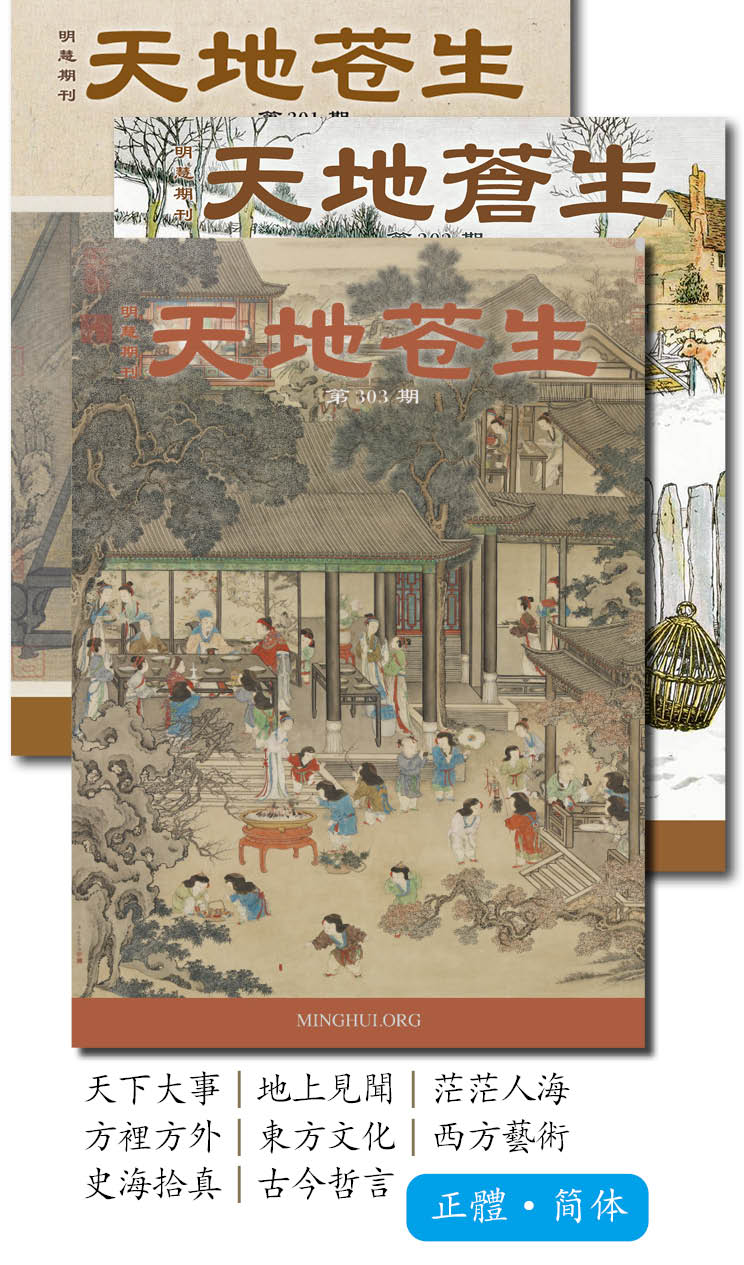五次非法劳教 北京农妇遭十年残忍迫害
在北京女子劳教所,二零零二年四月的一天半夜一点钟,恶警关闭了所有楼道的铁门,恶警焦学先(当时的三大队大队长)和恶警霍秀云和五、六个打手扒光郎东月的衣服,拳打脚踢,棍棒交加。这些恶徒还用牙刷对郎东月进行性摧残,把牙刷捅进阴道,乱挖乱钻,极尽流氓手段使郎东月痛苦。
二零零八年北京奥运期间,郎东月等北京法轮功学员被劫持在辽宁省马三家劳教所迫害,放回时,她的身体瘦小枯干,生活不能自理。
郎东月从小患有哮喘和全身的癣病,修炼法轮功才使她身体康复。她的癣病和哮喘原本几十年求医无效,任何农活都不能干,如果有一天能躺着睡十分钟的安稳觉,都觉得特别幸福。炼法轮功后,全身的病痛在极短的时间里都消失了,没花一分钱。
下面是郎东月女士自述这些年来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而遭中共迫害的大概情况。
我叫郎东月,是北京市延庆区延庆镇上水磨村人。我九八年六月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做好人,身心获得了健康。修炼不到一年,恶党就开始对大法弟子进行疯狂的迫害。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开始,恶警就让我交书,我拒绝。延庆恶警张海泉就带领镇里的人到我家抄书,我对他说:“书都在我心里,半个字你也拿不走!”恶警恶狠狠的说我是神经病,从此以后经常到我家进行骚扰。
九九年十二月中旬,我和几个同修为证实大法、还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到天安门去打横幅,被非法关押到延庆看守所,看守所恶警康健手拿一个小铁棍逼迫我们自己打嘴巴,我不打,他就拿铁棍敲我的锁骨,后逼迫我们脱掉外衣,只穿内裤或秋裤和背心,赤脚站在冰上,致使脚下的冰都化成了水,他还得意的问我们冷不冷,他穿棉大衣在屋里还冻得乱转。强迫我们站了很久后,他自己实在冻不起了要回办公室才让我们进屋,但不让穿衣服,并开着窗子让我们坐在木板上,直到天黑才让我们穿衣服。半个月后,我从看守所出来后再到天安门证实法,被抓到看守所后,因炼功被拳打脚踢、电棍电是家常便饭。曾有一次被恶警逼迫趴在木板上,我们挨着个的被恶警用胶棒打,满头白发的老太太也不放过。
第一次被劳教迫害
二零零零年四月我与同修再次到天安门去证实法,被非法抓捕关押一个月后非法劳教我一年。一到北京劳教人员调遣处,就让我们面朝墙站着,写保证的让进屋,不写的就总是站着或迫使我们低头并且还得抱着头蹲着,不让看人,否则就拽着头发拳打脚踢或用电棍电,腿蹲麻了晕倒就暴打一顿,强迫继续蹲着,吃饭时也不让站起来更不让坐着也不让看人,否则就暴打一顿。吃饭前必须背他们规定的二十三号令,还得唱饭歌,不背、不唱不让吃饭也不让睡觉。有一位大法弟子站得腿肿得很粗都蹲不下去,床也上不去了,吃饭时就让她头冲着地,身体成倒“U”型吃饭,吃饭时间仅三分钟吃不完就被夺走。上厕所必须排队并低头,手放在小腹部位,先大声说队长好,过一个门就喊一次报告,不管大小便三分钟之内,解不完也必须出来,否则就会遭到残酷的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喊队长或喊报告的声音小了都不让去厕所。如果抬头看看就会被恶警、吸毒犯们暴打或电棍电。有一个大法弟子就因为没有低头,被几个人揪着头发迫使她低头并拳脚相加,后被带到没人看见的地方进行更为残酷的折磨,再看见她时,她就被戴上了手铐和脚镣连在一起的刑具,身体只能成倒“U”字形弯着腰走路,大小便时极其困难。
 酷刑演示:“壁虎爬墙” |
后来我被送到了北京市新安劳教所迫害。一到劳教所就逼迫我写保证不炼功、检举别人等东西。因为我不写就强迫我白天黑夜都站着,我还是不写,就强迫我蹲着,蹲几天之后又强迫我白天黑夜做“壁虎爬墙”姿势(两臂上举,两手扶在墙上,右腿弯曲脚离地,膝盖顶在墙上),我不做那个姿势恶警就指使吸毒犯们对我拳打脚踢,接着又让我飞着,(头朝向地面两臂上翻,手贴在墙上)我的手没贴着墙,就被恶警指使的吸毒犯们一群人用红塑料底鞋的鞋底狠命的抽打我的手、脸等处,当时指使的恶警叫李守芬。那时冬天不让我盖被子。当时的大队长焦学先把我叫出去问我:你不盖被子冷不冷?我说是你不让我盖被子,不是我不盖,我有师在有法在我不冷。她就指使人把我的被子扔到劳教所的院子里,接下来她就指使小队长杜敬彬对我进行更为恶毒的迫害。
恶警杜敬彬对我说:我看你活腻歪了!你敢顶撞焦大!我拿绳子把你捆成球形,塞到桌子里头去。后来她就把我弄到一个单间,让我一动不动的站着,只要稍动一下就开始打,我被包夹们看着,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是那样。为了不让我睡觉,把我一只脚给拴上绳子,有人拿着绳子时刻盯着我,只要一合眼她立刻就拽绳子,因极度的困乏我摔倒了,她们就把我拽起来让我继续站着,直站到我的腿肿得让人看了直害怕,不能弯曲,走路时只能直着走,毛细血管崩裂往出淌血,腿部皮肤象透明胶条,象血腿一样。恶警焦学先看我实在站不了了,就指使刑事犯拿一褥子放在地上让我坐上去,由刑事犯对我读攻击大法攻击师父的邪书,昼夜不停的对我进行精神上的迫害。这期间,焦学先威胁我说:你不写就把你送到集训队去,你知道吗集训队就是拿电棍电阴道,用牙刷刷阴道。我不听她的,接着她就把我调到当时的第六大队。
那时第六大队的大队长是苏向荣,她是在集训队专门利用吸毒犯迫害大法弟子的恶警。因苏向荣有迫害大法弟子的经验,所以当时北京市新安劳教所成立了专门迫害坚定的大法弟子的六大队之后就让她去当大队长,把积极迫害大法弟子的恶警们都调到六大队。她们除了不让大法弟子睡觉、不让上厕所、让蹲着站着外,再有就是让吸毒犯恶毒的打,专打痛处。有个大法弟子是个漂亮的小姑娘,还是四级演员,她被扒光了衣服先被男恶警强奸,然后恶警又用电棍电阴道,这是两个吸毒犯闲聊时被我听到的。我当时就被折磨的骨瘦如柴不象人样。这是我第一次被劳教时所遭受的迫害。
第二、三次被劳教迫害
2002年1月我流离失所到北京市顺义区给一家农民打工。一天夜里我出去贴真相资料时被顺义恶警抓到,他们把我弄到派出所逼我承认那屋子里的光盘和横幅都是我的,我不承认。他们就迫使我只穿秋衣光着脚在派出所的院子里被一个烧锅炉的老头拽着在院子里走圈。后来又给我戴上手铐,把我吊到篮球架子上。
不知吊了多久,我晕过去了,他们把我弄到屋子里拽着我的手在他们写的东西上按了手印,给我头上泼了两舀子凉水又把我拉到外面吊起来,很长时间后又把我弄下来,拉到屋子里铐在暖气管子上,三个男恶警脱光了下身让我看着,还说把头扭过来看着,他们不穿下身衣服光着躺在床上。天亮后他们把自来水打开放水,水管周围冻成冰后把我铐在水管子上,脚踩在冰上。那天早上八点开始对我进行审问,我不配合把法轮章吞到肚子里,接着他们把我带到公安医院,他们还把我的家人叫到医院想要勒索,我不配合,后把我送到了看守所被非法劳教一年。一到北京劳教人员调遣处时被几个恶警电击后,把我和一个叫刘春华的大法弟子关在一起,五六个恶犯人把她按在地上。在大队长张冬梅的指使下,有人站在她的两只胳膊上,有人站在她的两条腿上,还有一个大胖子跪在她的胸部上,用牙刷把撬开她的嘴,把倒在半桶水里的一大碗饭、一大碗菜灌到她的肚子里,灌完后,让她站在距离墙有半尺的地方,张冬梅指使恶犯们轮番的跑向刘春华去踹她的肚子,那被灌的鼓鼓的肚子里的饭菜,又都被踹的从嘴里吐出来,踹了很长时间后让她站在一块方砖上。
然后把我弄到另一个屋子里,把所有的窗子都打开,地上泼上凉水,让四个吸毒的犯人把我的衣服都扒光,然后把我抡倒迫使我躺在泼了水的地面上,接着蒙上我的眼睛,恶警付文琪等几个恶警命令吸毒犯张德华、马强、雪梅、马利撬开我的嘴,把放好了药的饭汤子灌到我的肚子里,撑的我很难受直要往上返。这时问我穿多大号的鞋,我说穿三十九号的,付文琪对吸毒犯说,“给她拿二十二号的最小号的让她穿!”几个吸毒犯就硬是把我的脚塞到那小鞋里,然后前面有人拉后面有人踹,强迫我走路。后来把我关到一个小屋里让我蹲着干活,我不配合,接下来吃饭的时候,她们就把我的两只手绑在一张床的两个角上,把我的两条腿撇开,把我的双脚各铐在那张床的另两个角上,让又高又壮的吸毒犯跪在我的胸部,撬开我的嘴往我肚子里灌倒在水里的饭菜汤。
不写保证就那样被固定在床上不让大小便。张冬梅说不写保证就是不让你大小便!并不时的指使吸毒犯把绳子拉紧把铐子铐紧。后来又给我换一个屋子,在夜里没人看见的时候,扒光我的衣服强迫我坐在小凳子上,我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张冬梅就指使吸毒犯马强、雪梅把我下体的卫生巾拽出来,塞到我的嘴里,脏血就从我的嘴里流出来,我念发正念口诀,恶警张冬梅就让马强、雪梅去厕所找最脏的卫生巾再塞到我的嘴里,张冬梅还说:“她要再喊就给她往头上倒凉水!”当时我的胳膊被拧到身后,两块卫生巾塞在嘴里我已经喊不出来了。我被拧着胳膊坐在小凳子上直到天亮。腿脚都冻得发紫,并冻出了疙瘩。后来白天让我坐在大凳子上,只要稍微动一动,马强和雪梅就开始打我。
夜里没人看见的时候,张冬梅就叫四个吸毒犯把门关得紧紧的,撇开我的两条腿,往我的阴道里塞东西,拧着我的胳膊不让动,直到后半夜才给拽出来。第二天同头一天一样折磨完后,又把我扳倒按在地上,恶警付文琪拿水直接灌我,并指使张德华把着我的一只手,马利拽着我的另一只手,写了所谓的保证书。写完后强迫我继续光着身子坐着在椅子上冻着。白天怕别人看见才让我穿上衣服。这是在北京劳教人员调遣处的事。
2004年正月,延庆派出所恶警段磊等人与恶人杜明华、杜富栓相互串通,无故将我抓到看守所,一个多月后非法劳教我两年半,被直接送到劳教所的集训队,遭受到不让上厕所、不让睡觉的迫害。其他的迫害不再详述。
第四次被劳教,在马三家遭受非人折磨
2007年我在去北京市劳教所发正念的路上,被恶警绑架到延庆看守所。我不断的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女恶警赵瑞玲唆使号内的嫌疑犯王珊等人扒我的裤子,把裤子撕成两半后,有踹胳膊踹腿的,有用一条裤子褪勒我的脖子勒嘴的,勒的我喘不过气来,同时还有往我身上倒凉水的,折磨了好长时间,到晚上八点左右,吸毒犯并同性恋王珊看我发正念就不让我立掌,我不听她的,她就把鞋甩向我,鞋没打着我,可是她的胳膊却脱臼了。到医院也接不上,她亲身体会到了大法的神奇后,明白了真相离开了看守所。
我又被非法劳教两年半,接着被送到了调遣处。当时的大队长张冬梅指使包夹不让我上厕所、不让我睡觉,还强迫我劳动,不听她的就用塑料尺子敲脚踝骨、锁骨等痛处。有一个叫俾(同音)秋月的吸毒犯在我没有防备的情况下狠踹我的后背。有一天她与吸毒犯杨佩华配合,把褥单拧成绳一人拽一头要把我勒死,还有一天早上邓丽娜、俾秋月、杨佩华等人无故对我拳打脚踢,队长张冬梅来后变本加厉,唆使包夹用毛巾堵着我的嘴把我弄到没人的地方摔倒,杨佩华踹我的胸部,俾秋月、邓丽娜踹腿,还有的用拳头砸我的脸,直到她们打累了才罢手,打得我浑身上下都是黑紫无一好处,并且不能行走了。后来从大队长到包夹都遭了恶报。
一天半夜里,恶警把我叫醒弄到车上,给我戴上手铐,恶警苏向荣还给我的头上戴上一种很难受且不能说话的刑具,拉往辽宁省马三家劳教所。一到马三家劳教所就看到黑压压一片手持电棍头戴钢盔的男警察。一下车我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立刻一群象毒马蜂一样的男恶警向我扑来,一个恶警拽着我的胳膊往走拉我,其他的一路上有电嘴的、有打脸的、有踹的,在上台阶的时候,一恶警猛踹我的左腿,到楼上后我的脸被打得满脸青紫,眼睛睁不开了,腿也无法行走了。接着又进来四五个面目凶狠的男恶警,恶狠狠的手里掂着刑具对我说:这里是马三家,你以为是北京呢?你不遵守这里的制度就让你尝尝马三家的滋味!我说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我不要、也不承认!一个恶警拉着我的手他们把我铐到距地面两米高的床上,我被吊了起来,我不断的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他们又给我戴上了开口器,我的嘴被撑的难受极了。他们把门关上离开了。
 酷刑演示:吊铐 |
在极度难受的情况下,我求慈悲伟大的师父让开口器坏,我这嘴是证实法的,瞬间头后边开口器的弹簧就开了,嘴里的开口器缩成了一小点,我把它吐了出去。我再求慈悲伟大的师父把手铐给我打开,立刻给我上刑的那个人就进来了。一进来所长就说;“谁给她把开口器打开了?”另一恶警说:“都在外面忙着,钥匙不是您拿着吗?”这样他们打开了我的手铐。然后把我拖到全是大法弟子的屋子里,大家互相鼓励一定要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在那屋子里我看到有的大法弟子被打的鼻青脸肿、面部走形。北京的李利和苏微就被吊得两个胳膊的肉都烂了,还往出流血和黄水,胳膊都不会动了,双腿都不能行走,脸部青紫。还有全身肿的象在水里泡的一样发白透明。
还有一个六十多岁的大法弟子,被迫害的右臂骨折,大小便不能自理,吃饭的时候我看见她用一只手和一只脚撕卫生纸。第二天早上去饭堂吃饭站队时,男恶警头李勇手里拿着电棍,看谁走的慢就电谁,有的大法弟子被打伤了走的慢,谁要是扶一下就会被一起电。到门口要唱饭歌,谁不唱立刻就被拉走酷刑折磨。吃饭十几分钟,还包括洗碗、扫地,收拾完后立刻站队到一个屋子里坐在小凳子上,有一姓严的男恶警给念破坏大法攻击师父的邪书。他念完后再让大法弟子挨个的念,谁不念就被拉出去酷刑折磨或面墙而站或被吊在床上。大法弟子张连英不念,立刻就被拉了出去。后来第二天下午吃饭时她被两恶警一个拉一只胳膊拖回睡觉的屋子,扔在床上,四肢被吊的不能动了,面部青紫,眼睛不能睁开,上嘴唇被用铁勺子砍豁了,大家以为她被折磨死了,都上前去呼喊她,她用微弱的声音告诉大家:“我没事”,碰她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她都疼的难以忍受。
当轮到我念时我说:“我念的是宇宙最正的佛法,你念的都是破坏大法的邪书,我不念!”立刻进来一个恶警和一个地痞无赖,把我拉进一间放有各种刑具的屋子里,屋内至少有七八个恶人,李勇指使着恶警和打手们电我两腿内侧、还有从后边踹我的腿和背部的。把我踹倒后,恶警李勇问我念不念,我不配合,把我拉回去让我站着,我就坐在地上,逼我站起来我也坐着,我说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其他的安排我不要不承认!从此以后再不让我念那邪书了。后来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令别人不可想象的让我到车间去剪线头了。有一天一个大法弟子给我经文被吸毒犯郑戴玉看见后举报,队长张宇把我叫进一间屋里,一进屋她就左右开弓抽我脸,我的嘴被抽的流血,把我踹倒后又拽起来,她指使犯人把我拉到恶警的宿舍,一进屋她就接着抽我的脸,边抽边说把给你的东西拿出来!不拿出来就把你铐在椅子上电你!她边说边拿电棍,电我的嘴和脸。这时恶警的大队长王树征进来也是左右开弓抽我的脸,边打边对恶警张宇说,拿最小的铐子,然后拿着电棍和手铐往外拉我,又拉到一间有刑具的屋子,一进屋恶警王树征电我,恶警张宇一边扒我的衣服一边搜别人给我的经文。在拉我去那间屋子的路上,我就求师父别让恶警看到经文,我想到了师父的小传,就想她就是用电棒照她也看不见!结果衣服都扒光了她也没发现那篇经文。后来她们就捆我的腿,从脚脖子捆到大腿根,捆完后往酷刑床上拉我,把我的左手铐在最上边的床头上的一角,右手铐到左手斜对角的最下边的一角。她们狠命的拉才铐上,手与手之间有很长的距离,铐上之后她们两个一起用电棍电我的脸、嘴,直电到吃中午饭的时候,才把我解开。手被铐的不能弯曲,腿被捆的不能走路。后来又一次,我在车间唱《法轮大法好》这首歌,一个姓任的女恶警指使人把我拉到库房,她先用手抽我的脸,她手打疼打累了,就用笤帚把打我的手,脸,腿,狠命的打,打累了,她就坐在凳子上歇着,我身上被抽的都是一道道的血印子,手,脸都是青紫的,笤帚把都打飞了。后来我去洗澡时把别人吓得大声喊叫,晚上睡觉时,有人对我说:“阿姨你把身上盖上,我害怕,睡不着。”
那一年“四二五”的头两天,大家一起证实大法,一起喊了“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恶警张宇和大队长王树征,还有姓任的恶警挨个的问谁带头喊的,没有一个人供出,多人被酷刑折磨,我也是如此,被上了大挂。上大挂就是一只手被铐在两米高的床上的最上边的一个角上,另一只手铐在铐着那只手的那个角的斜对角的下边的那个角上,两条腿一起被绳子从脚脖子捆到大腿根,两腿在床栏杆的里边,身子在床栏杆的外边,下边那只手和铐在床上的铐子之间有一段只能站一个人长的一段铁链子,一百三四十斤体重的女恶警王树征站上去,咬着牙瞪着眼看着我,两脚不停的交替着狠命的踩那段铁链子,姓任的总管用手抽我的脸,嘴,恶警张宇用最大的电流不停的电我的脖子和胸部,肉都被电黑了,并起了大泡,散发出难闻的烧焦肉的气味。恶警们就这样折磨我很长时间,直到她们累了才罢手,指使别人看着我,我被继续铐在那里,直到下午两三点钟才把我解下来,那是从早上八点钟左右开始的。解下后我一下就倒在地上了,腿不能站,胳膊没有知觉,十指弯曲,躺在地上不能动。三个恶警把我拉到车间,让我干活,那种情况下只能是别人替我干了。后来还给我延期一个星期。
在那期间我还亲眼看到了三个大法弟子被折磨的情况。一次吃饭前,恶警让背那里的规范二十三号令,一个六十多岁的大法弟子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男女恶警立刻蜂拥而至拳脚相加在她的脸上、身上,打倒在地后脸被磕破,鲜血直流,男恶警拽着她的两只胳膊拉她走,身子和腿被拖在凹凸不平的地上,眼看着衣服很快就被磨破了,血从衣服里渗透出来,这时恶警们还在一边走一边打她,她被打得披头散发,就这样被拖到酷刑屋内。在酷刑屋内发生什么事我到晚上十点多钟,我们收工回监室时,才发现她五官走形,嘴被一个叫张军的女恶警用扇子把给抽破,身上的衣服破烂不堪,后背、屁股、腿上都是血迹,我们刚睡下时,听着她疼痛难忍无力的呻吟着,问她她用微弱的声音说,张军拽着她的头发往墙上磕、往铁东西上磕,磕得她头上全是大大小小的硬包,她的眼睛不能睁开,头里面嗡嗡的响。她呻吟了一会就再也没有声音了。狱医匆忙的进屋用听诊器给她听了听,就匆匆的走了。紧接着她被恶警李勇带领的几个人给弄走了,走时她的头已经耷拉着了。
还有一位叫殷连英的大法弟子,六十多岁,因她不戴胸牌、不吃饭,就给她灌食。恶警李勇在给她灌食时,因她不张嘴就用铁勺子把她的嘴给砍成两半,并电击她的全身,后来一有空就去电她,电得她大小便失禁,把她铐在铁门上日夜站着。
还有一个叫吴叶菊的大法弟子,因晚上十二点叫醒大法弟子发正念、证实大法讲真相,多次被酷刑折磨。衣服被撕烂,面部青紫,嘴被电得肿得不像样子,还流着血。被解教时,被接她的派出所的恶警和洗脑班的恶人们给塞到车的后备箱里带走。我离开马三家劳教所时听说张连英、张印英、盛连英等许多坚定的大法弟子被关到阴暗的屋子里用各种刑具迫害。这是我在北京调遣处和辽宁省马三家遭受的迫害。
第五次被劳教迫害
2010年6月我发真相材料时,发到便衣手里被举报,又被延庆县恶人劳教两年半。一到北京市女子劳教所我喊“法轮大法好”时,当时的护卫队大队长王金凤就捂着我的嘴,把我拉进医疗室,指使别人扒我的衣服的同时她电我,接着她又叫去七八个护卫队的男女恶警一起电我,一男恶警把我踹倒,他们就蜂拥而上,施暴后把我弄到四大队。
恶警杜敬彬等人把我拉到专门迫害大法弟子的包房里,揪头发扒衣服让我写保证,四五个恶警把我的头发剪的乱七八糟。恶警宋静跟我说:“你所有要干的事,都必须向看着你的人打报告词,她们让你去你才能去,过门时都要喊报告,打饭时两手端着盘子打报告词,必须说我是劳教人员某某某请求打饭,腰必须弯到九十度,不给打就面对墙站着。我不配合她们,因此不让我出屋,大小便也在屋里。而且刷牙、洗脸、大小便等用水都用一盆水,两个多月后调到大班。在大班,早上起床后晚上睡觉前都点名,叫到谁的名字谁必须答到,答到时必须蹲下、低着头、两只手抱在膝盖上。我不配合,姓鹏的恶警就把大队长杜敬彬找去让全班人都蹲着,长时间不让站起来,她想让班里的人都恨我,搞群众斗群众那一套。几个月后把我调到集训队。管班恶警于淑英让我天天在零下十多度的冷屋子里天天对墙站到半夜站了一个多月。后来换成恶警张清管班,一天她指使看着我的赵爱霞、梁博亚狠命的拽我的胳膊,她自己把着我的下巴往起搬,没达到她所要达到的目的,她还气的直骂赵爱霞和梁博亚,她管班期间,让我在我呆的屋里大小便。
后来又来一个叫李守芬的恶警给我限制大小便的时间,一天按她规定的时间我没解完,她就去掐我的脖子,按着我的头往铁管子上磕,磕完又按着我的一只手另一只手铐我的嘴,把我的嘴扣流血,还给扣下一块肉,她又在赵爱霞的帮助下,把擦大小便的毛巾塞到我嘴里。接着又把我弄到班里,乘我不备之时把我摔到床上,还是往我嘴里塞毛巾,从八点多到夜里一点才罢休。
其它的迫害,还有往我头上倒开水、把四五个牙刷绑在一起刷我的阴道等,由于时间太长,我已记不清是什么时候、谁干的了。
从1999年到2012年我被非法劳教五次,被关在劳教所里十年,这十多年我的儿子从一个小孩儿到一个娶妻成家的大人了,我现在已经回到家里,有了人身自由,可我的儿子却由于受邪党的恶毒宣传毒害不让我进家门。这个恶党不但迫害我,还迫害我的儿子,它迫害了太多的中国人,它让很多人失去了人最起码的良知和道义。但是退党大潮波澜汹涌,太多的中国人也在这场史无前例的疯狂迫害下认清了邪党的真面目,“天灭中共恶党”就要来临,善良的中国人必将迎来一个没有邪党的自由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