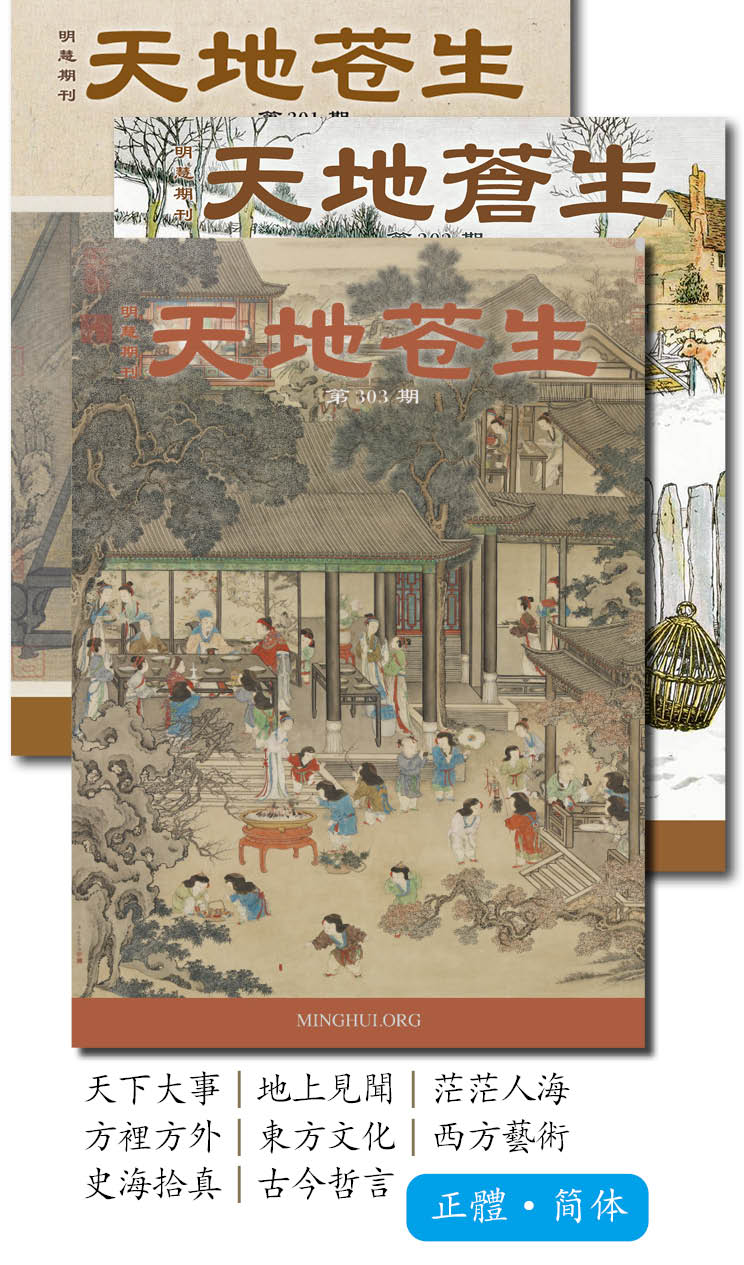修法轮功祛顽疾 检验师遭迫害历经生死
修炼法轮大法 顽疾消失
在修炼法轮功以前,我是一个事业心很强的人,为了事业,我二十八岁才结婚,新婚后三天,我又投入了紧张的工作。那时我丈夫是青海部队的现役军人,我婚后,两地分居五年,我没有请一次探亲假(本应每年有两个月的探亲假)。二十八岁结婚,第一个孩子却去医院作了人工流产手术。术后休假十五天,又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一天起早贪黑,因操劳过度,这样几年下来,使我身体遭受极大损害,患上多种疾病如:乙型肝炎、肾炎、左眼病毒性角膜炎、角膜溃烂、萎缩性鼻炎等。经多方医治效果不佳。因长期受疾病的折磨,家庭经济很紧张,维持基本生活都困难。为报销一部份药费,单位和公医办对我意见非常大。一九九一年,因紧急的工作任务压来,过度劳累,乙型肝炎、眼病等加重。我去县人民医院住院医治,别人却在我的账上记了药费(我不知道),出院时账单上的数目为三千一百元。结果单位和公医办不但没给我报销,还要行政处分我。多年工作的成绩被科长一把包走,她还向单位领导反映说付汝芳生了病,没做多少事。我觉得活在这样的世上失去了人生意义,我曾几次想到了死。但看到身边那个才几岁的儿子,就下不了那个狠心了:不能把痛苦压在孩子身上,应该尽自己当母亲的职责。
在我绝望之际,一九九六年六月,我喜得了法轮大法。我严格用“真善忍”要求自己,心灵得到了净化。修炼两个月后,我全身的疾病消失了,从此甩掉了药罐子,没有再报销过一分钱的医药费。工作干得井井有条,更加出色,我整天忘我的工作,却毫无怨言。单位上的群众都说我是个最好的好人。我身心健康了,我家里也充满了欢乐的气氛。
北京上访迎接我的是拳头铁窗
可是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以来,江氏集团在全中国的广播电台、电视台、报纸杂志等栽赃陷害、恶意攻击诬蔑诽谤法轮功及其创始人,信仰“真善忍”的群众遭无辜迫害。为了证实大法,二零零零年一月二十三日我到北京上访。迎接我的是拳头铁窗。一月的北京,天寒地冻,天安门派出所的恶警却将电风扇开到最大档,朝我们这些衣衫单薄的上访学员猛吹两个多小时,不给饭吃,也不给水喝。当被转到重庆驻京办,恶警查出我包里的一条横幅(“法轮常转”)、一个法轮图形和一百四十元钱。恶警当即对我没头没脑的一阵猛打,打得我头晕眼花,约有十多分钟头脑一片空白。窗外的积雪一尺多厚,我们男女老少十八名法轮功学员在一间办公室的光地板上睡了三夜,不给我们任何被褥,其中还有两位来自重庆北碚的八十多岁的老人。
二零零零年一月二十六日早晨,潼南县派恶警唐守峰和卫生防疫站副站长刘志德到京接我和其他弟子回去,回家的路上,恶警唐守峰让我们向其它地区不认识的法轮功学员借钱八百三十元,说是要支付路上的一切费用。事后得知,潼南县公安局的张良早在一月二十四日就已经向我单位敲诈了六千元作“遣送费”(后在我工资中扣除);张良还曾向我丈夫敲诈过钱,我丈夫说:“我是个下岗职工,哪里去拿钱给你?”
二零零零年一月二十七日晚,将我送入潼南县到看守所。我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三十三天,期间遭多次抄家。恶警抢走大法书四本。二月二十八日看守所发了释放证书给我,说放我回家。不料,公安局张良、李永红等又直接将我关进拘留所八十五天。还敲诈一千元保证金给张良,四百二十元生活费给拘留所,才将我带回家。
在劳教所黑暗的四百三十天中受尽折磨
回家才七十天,二零零零年八月二日上午九点,张良、钟明、刘勇、罗永红、李恒毅等又闯入我家,张良当着我丈夫的面说有件事找付汝芳去公安局核实一下,一、二个小时就回来。一到公安局,张良就给我戴上手铐,逼我承担七月十五日县城出现张贴法轮功真相资料的责任。晚上将我关押在县城一派出所,与犯罪的男人(有嫖客、吸毒的、打架的、偷窃的)关一个房间,连续四天三夜不准我睡觉。
八月六日下午五点,我被押到拘留所非法关押五十天。八月十六日恶警张良到拘留所找我谈话,我告诉恶警我没有触犯国家的任何宪法、法律,要求:1,立即无条件放我回家;2,以后不能任意再来绑架我。我说,你们这一伙人这样绑架好人,是在犯罪,并当面揭露了将我与男犯关一个房间的犯罪行为,是对人格的侮辱。我为了反迫害进行第一次绝食抗争,但我看到别的学员被野蛮灌食的场景太残酷,没能坚持到底。
二零零零年九月二十四日公安一科的罗永红等将我从拘留所押送到看守所。第二天,在我没签任何字的情况下,我被从看守所送到重庆茅家山女子劳教所。黑暗的四百三十天我在劳教所受尽折磨。我在劳教所绝食四次,并多次写上访信。二零零一年九月二十七日,劳教已超期五十五天,潼南县二派出所刘朝礼才来接我出所,但又被劫持到潼南县拘留所。在拘留所我向潼南县六一零负责人写了抗议书,并又绝食抵制,于二零零一年十月七日才回到家。
在劳教所,我经受的酷刑折磨的残酷是我们外面人无法想象的。我作为一个法轮功学员,以对大法和师父的坚信,以自己从大法中修炼出的钢铁般的意志,一一闯过来了。
中共开十六大 遭绑架 死而复活
二零零二年十月二十九日下午三点,我正在单位上班,恶警张良等闯入我的办公室乱翻,尽管什么也没翻到,还是将我强行绑架上警车,并送拘留所。之后又抄了我的家,抢走法轮功讲法光碟、炼功带及《转法轮》书。我从劳教所回家一年来,还是与往常一样,一直在单位兢兢业业的工作,只要工作需要随叫随到,经常加夜班,没有半点怨言,也没有向单位要一分钱的加班费。不仅如此,我的工资比同等职工每月少三百七十四元,我也没有计较。这些恶警为什么来绑架我?后来我才知道,张良给我单位领导说:“江泽民要召开十六大了,又下令抓捕法轮功。”我绝食抗议。
 酷刑演示:野蛮灌食 |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五日上午,恶警张良给我强行野蛮灌食,灌得我肺里的鲜血直往外冒,才给拔掉管子,给我安上氧气管,这时我才喘过气来。
随后张良将我送县医院照了X光,张良为了推脱责任,叫放射科医生写假报告,说没有灌到肺里,还叫医生乱编造,说我炼法轮功炼出了心脏病,并且到处传此谣言。张良又将我往拘留所送,途中我频繁呕吐,但又未吐出东西来(因胃里没有东西)。到了拘留所,张良叫人把氧气管给我取了,又把我关入五号室。不到二分钟,我就呼吸困难,胸部剧痛,心里慌,难受,头眩晕,口中吐鲜血,房间的人说:她嘴唇发乌,立即报告值班警察;拘留所廖所长、刘干事来看到此情况,又叫来了张良,把我立即又送县医院。
在县医院门诊大门处,医生已经摸不到我的脉搏,量血压也无反应;听人说我面色青土色,手指发乌,手脚冰冷。我丈夫被张良叫来,张良看见我已经不行了,怕承担后果,就把我交给丈夫,张良自己就缩头了。县医院的彭软医生给我丈夫说:“此人凶多吉少,抢救看有没有效。”并发出病危通知书。我丈夫将我送到抢救室,抽血化验,报告“酸中毒”。为了防止恶人下毒手,我要求回家。我从抢救室出来时,并没有脱离危险,身体极度衰弱,要停顿几次,才能说完一句话,咳嗽无力气,咳不出,擤鼻涕也没力气,擤不出;双肺区剧烈疼痛,好象失去了功能。我被迫害得死而复活,是师父救了我,我才活下来了。谢谢师父的又一次救命之恩。
我在县医院只呆了六个小时,我丈夫只取了一百一十七点九元钱的药(一张处方,输液的费用),化验费一百元。可是张良于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十四日给我单位领导打电话,说我在医院用了一千多元的药费,还说我开了药拿回家等。第二天我给单位讲了实际情况,将处方给领导看了,揭穿了张良的谎言;并且我还给单位领导和公医办负责人说:“我不承认这笔医药费。”恶警光天化日下把正在上班的我绑架去,迫害得濒临死亡,难道还要我给他害人的工钱吗?后来张良找潼南县副县长蒋道义批了条子,在我单位强行报销了二千多元。
上诉冤情遭牢灾 法院不能鸣冤
张良一伙对我无端迫害,我把他们的犯罪事实向检察机关写了个投诉材料;因页数较多,二零零四年七月十六日中午,我把材料拿到潼南县卫生局门口打印店去复印,复印完走后,复印店的人害怕公安局来追查他的责任,就给我单位办公室主任唐述先反映了此事。随后办公室主任唐述先将我复印上诉材料的事向二派出所恶意举报了(举报一个法轮功学员,中共给一~五千元奖金,引诱世人犯罪)。
七月十九日上午,潼南县国安大队罗永红等、二派出所恶警来到我单位,与卫生局和本单位领导在会议室坐了一屋,将正在上班的我叫去,叫我交出复印的上诉材料和原手稿。我说:“我依照宪法办事,我有上诉和说话的权利,这是宪法给予公民的基本人权。”他们哑口无言。接近十一点钟,国安大队袁学平、罗永红及派出所几个恶警又把我强行绑架上警车送二派出所,并且强行抄了我的家,没出示任何手续,把一本手抄经文抢走了。张良在二派出所坐镇指挥,派人给我做材料,以莫须有的罪名“扰乱社会治安秩序”判我十五天拘留。在派出所,连续二餐不给我任何东西吃,我又饿又渴,袁学平等还冷笑说:“你告嘛,怎么告不准呢?”七月十九日下午六点多钟将我送到拘留所。
从七月十九至二十二日,在那三十五~三十六度的高温下,我四天绝食绝水,可还要我每天交十元生活费。七月二十二日上午,张良派李恒毅和二派出所给我编造材料的恶警来到拘留所,编造材料那恶人恶狠狠的吼道:“错的也要执行,不吃就强行灌,把你整死了我们不负任何责任。”下午,被拘留在同舍房的一人对我说:“大姐,你不吃饭,他们又要强行灌你,又要强迫我们来按你,我们不来按,他们要处罚我们。二零零二年那次我按你时,看见把你灌得鲜血直流,都差点把你灌死了,我们要带过(造罪)啊,我们该怎么办?”
说我复印上诉材料就是“扰乱社会秩序”,这是潼南公安局在违法。我于二零零四年八月六日向重庆市法制办写了申诉。十月十五日上午九时四十五分,国安大队李恒毅、罗永红给我送来《行政复议决定书》(公复字第4178号)。重庆市公安局长朱明国与潼南县公安局局长殷建中同流合污,庇护潼南县公安局的非法裁决。《行政复议决定书》的下端写有“如不服本决定,可在接到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法律规定应是十五日内)。十月十九日(五日内)潼南县人民法院立案庭接受了我递交的起诉:公安局局长殷建中的材料,当时说等候通知。我将座机电话、手机电话留给了立案庭,等立案时再去交诉讼费。并于十月十七日已将此材料用特快寄重庆市中级法院和北京最高法院。
可直到二零零四年十一月十五日都未得到通知。我再次去法院询问,可潼南法院立案庭庭长叫我去接待室。接待室那人说:“上面已来通知,法轮功的不能立案,不用文字回答,只能口头回答……”问他哪来的通知,他也说不出来,也拿不出通知来。还叫我不要去找他们了,去找该找的地方说理。问他去哪个地方,他说不知道。我说:“就是应该找法院为民鸣冤,《行政复议决定书》上就这么写的。”他说:他不能为法轮功学员鸣冤。
这是什么世道,民众有冤无处申,有理不准说。法院不能为民众鸣冤,到底是干什么的?
第五次绑架第二次送劳教所
二零零五年四月八日我在回老家上坟途中被跟踪绑架,(事后才知道是我单位的袁乃良、王奕锦、唐述先合伙去举报,说我跑北京了。因我走前,去向王奕锦(那时她是我科室的副科长)请了一天补休假。我绝食八天闯出看守所,五月二十二日,又遭突袭绑架并二次送重庆茅家山劳教所,不到一个月,已被迫害得门牙掉两颗,瘦得皮包骨,身体极度虚弱。
两颗下门牙被撬掉
在劳教所,我经常被包夹(吸毒犯人)打得周身青一块紫一块的。我开始有两天没吃饭,因胃被整成了胃炎,随后一顿吃了一两勺稀米汤,恶警就安排五个包夹吸毒人员给我强行野蛮灌食,连续灌了近半个月的稀米汤及不明药。有三次被灌到气管里差一点丧了我的命,我不配合灌食,吸毒人员将我的下门牙撬掉两颗,当时鲜血直流他们也不管,还继续灌,鲜血与稀饭从我脸上流到耳朵,经过头发流到地上,靠头部那一块地都是鲜血,吸毒犯人丁岚还说要把我满口牙撬掉。
灌食后还要不能走路的我起来打扫地板,但就不准我洗自己身上的血和饭汤。每次灌食给我脸上、头上、衣服上染上的血、稀饭和药水都不准我洗,每次灌都将我自己的衣服穿上,灌了又脱下放在地上,下次再灌再强行我穿上,反复这样,弄得衣服粘满了血、稀饭和药水,看不到一点衣服的本色,臭烘烘的,无法穿了就甩掉,这样甩了四件衣服。我的口腔内和嘴唇被吸毒犯人用瓢儿和手指捣得溃烂,嘴唇外都是血糊糊的,嘴唇和脸也都是肿的。
更甚的是,吸毒犯人丁岚用手指钻我的口腔时,手指在牙齿上刮伤了皮,恶警大队长谭清月当吸毒犯人的面恶狠狠骂我,骂我把包夹的手指咬伤了,有意滋长吸毒犯人对我的迫害,我的两个腋下被吸毒犯人用手掐得溃烂。我有一个多月没有吃一点盐。并有一个多月没有解大便。我被折磨得只有一张皮包着一具骨架。吸毒犯人自己都说:晚上我睡着了就象一具骨架摆在地上,看到都害怕。
我白天走路要人扶,或我自己扶着墙壁走,夏天那小间恶劣的环境使我周身长满了痱子,并且常常发高烧,可就这样的身体还是照样整训,我站军姿站不起,倒了几次,吸毒犯人说我装的,又将我拳打脚踢的打一阵,又强行我站,随后我双脚水肿至膝盖上面,象大象的腿一样,以后全身浮肿。发高烧烧到三十九点五度,还要强行我做军蹲,晚上十二点都不准我睡觉,吸毒犯人常体罚我做下蹲,不管我的高血压病,经常叫我长时间军蹲不换脚。
洗脑
恶警还对法轮功学员强行洗脑,每周星期天晚上要写思想汇报,被认为合格才能睡觉;强迫法轮功学员看诽谤大法的书、电教片,写感想,每隔一个月或两个月要开一次揭批会。
我每天晚上被强迫写思想汇报,恶警只给半小时的时间,晚上十一点半钟才叫我开始写,写得不符合要求又强迫我重写,不准睡觉,包夹丁岚(吸毒犯)常打我,常体罚我,这样折磨了四个月,我精神都要崩溃了,一直折磨到我写三书,所部来人验收合格为止。验收合格后才离开小间下组干劳役……
生病的遭遇
二零零六年四月我身体被残害成了伤病,我看到张秀云生病落得“诈病”的罪名还要被整训,所以我对谁都未说,强忍着,后来被别人发现,报告了恶警,恶警罚我写检查,随后将我弄去所部医务室检查,又去大坪三军医院外诊,肉眼都看见我整个小腹部位变紫变绿了,还有两个很硬的肿块,人枯瘦如柴,体重近七十斤,医药费用了两千多元,但效果不好,恶警也从不告诉我是什么病,我小腹常阵发性的疼痛,小腹胀,疼痛得心里发慌、难受,有时痛得面色苍白、休克,随后肛门常流水,劳累了也有休克的症状。四月二十九日恶警又弄去大坪三军医院外诊时,我都听到医生给恶警说肠有恶性病变的症状,准备去做CT检查,但要一千多元钱,没有那么多钱,就未做CT检查。大队恶警代文娟、陈用莲还找我谈了话,打算让我保外就医,可随后又变了卦,说我思想有问题。恶警分队长左靓晶将我叫去狠狠地说:打消你回家的念头,你现在还能走路,想回家就是抗拒改造,炼了法轮功就应该承受等……
第二次劳教遭迫害比头一次还残酷许多,迫害事实真是说不完、写不完,太多了。
我二零零六年十一月该回家了,但身体被迫害的极度虚弱。回家那天,我家里亲人(儿子、丈夫)来接我,劳教所不放人,说我“转化”的不彻底,要单位保证接回后,还要对我严格监控。
潼南县疾控中心(卫生防疫站)单位领导伙同恶警迫害
我的身体被迫害成了绝症(癌症),回家后经常小腹疼痛难忍,常常解血大便,不解便肛门还经常流水,我一直在家养身体。可中共邪恶没放过我,还常来骚扰我。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八日下午四-六点,七、八个恶警经我单位领导允许来撞门而入到我家乱翻。来的人有:潼南县国安大队的罗永红,潼南县梓潼镇建设路派出所所长及成员、潼南县梓潼镇陈家托街道办主任等,抢夺了我和我儿子的电脑笔记本各一台,抢走了我的手机、u盘、mp3等东西。至今未还。骚扰得我在家呆不下去,我的身体正在恢复期间,需要安宁的环境休养,我为了生存,只有离家出走。国安恶警给我单位的刘志德(书记)说在我家门口安个摄像头。我有家不能回。
我单位领导(现任疾控中心主任王浩、副主任郭大勇、副主任杨秀明)配合恶警到处找我,并且今年(二零一一年)六月起,将我仅有微薄只够我个人生活的退休金给停发了,每个职工享有的过节费也未给我一分,借口是:逼我回单位写“三书”。在六月停发退休金时,王浩把我丈夫叫去,给我丈夫说不能为了付汝芳一个人影响整个单位。还叫单位职工见到我,去报告领奖金。单位领导配合恶警把我迫害成了绝症,不但不给予医治,还不给我发工资,不给我饭吃,他(她)们就这样伙同邪恶犯罪,来剥夺我的生存权。
二零一零年,重庆市女子劳教所的恶警陈宴颜在付汝芬非法劳教期间,她给付汝芬说:你妹妹付汝芳回去没有死,可能是重庆大坪三军医大诊断错了。
遭经济迫害约十多万元
我单位那些当官的,看重自己的官位,为了自己升官发财,不听法轮功学员给讲的真相,出卖良知,他(她)们与邪恶助纣为虐,伙同邪恶一起来迫害法轮功学员。不但编谎言常去汇报我,得奖金,而且又在经济上直接迫害。
我修炼法轮大法前疾病缠身向国家报销药费,修炼后身心健康了,十五年多为国家至少节省数万元医疗费,却反遭中共恶警一伙敲诈钱财和被单位克扣工资总计约达十多万元。(不包括单位所交遣送费六千元、所谓药费二千多元)
一、火车上平均一人交了二百零七元、保证金一千元、拘留所生活费四百二十元。(手中共交出一千六百二十七元)
二、被非法关押共一千一百三十多天,其中有五百四十天未给我一分钱的生活费和工资。(应领工资近二万元)
三、连续二次未给我调资(在非法关押期间一次,回单位上班以后一次);二零零一年十月上班直到二零零三年六月,每月工资比同等职工(一千零七十八元)少三百七十四元,只给了我七百零四元。(这段时间少给我工资七千八百五十四元)
四、二零零三年六月以后,我比同等职工少三个档次。二零零三年六月-二零零三年十二月,每月少给一百五十元。从二零零四年元月后,每月少给我一百三十元。(两次共少给一千四百元)
五、二零零六年十二月调资,我本应调薪级工资二十九级,(那年是李宏当疾控中心主任,李宏看到我一直为单位兢兢业业干了三十多年,为人又忠厚善良,经济已经损失这么大,就把我的工资更正过来,表面上单位都通过了后,将调资表报县调资办去了,还没批下来时,疾控中心的人(袁乃良、唐述先伙同财务科科长冯桂华:手机18996022696)又去举报,就把我的工资又搞下来,并且随后李宏的疾控中心主任职务被不明不白免去了,后来任了个闲副职)就只给我调了十五级薪级,比同等职工每月工资少四百多元接近五百元,这次调资是从二零零四年补发,直到至今是七年,每年少给我工资六千元,七年少给四万二千元
六、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八日下午恶警在我家抢走了我的手机、u盘、mp3及两台手提式电脑等。手机:1000元、mp3四个,单价一百四十元,五百六十元、u盘一个五百元、两台电脑一万元、USB2.0:100元、无线上网卡:1200元。计:13360元。
七、二零零六年四月在茅家山劳教所我被残害成了癌症,医药费用了二千多元,
八、恶警几次撞门入我家抢走我的私人财产:讲法录像光碟、炼功磁带、书等约五百多元。
九、二零一一年六月起将我的退休金、过节费给停发了。
我二零零四年已递交材料,请求法院帮助我讨回二零零四年以前这些被非法敲诈、侵占的个人财产,但一直没人理睬此事。在此又一次要求给予赔偿和偿还恶警对我精神上的迫害和身体上对我迫害造成损失的赔偿金,及偿还单位扣发我的工资等。
潼南县疾控中心参与迫害付汝芳的恶人如下:
现任重庆市潼南县疾控中心主任王浩:手机13668063366、18983382307;
副主任郭大勇:手机18996022716;
副主任重庆市潼南县疾控中心杨秀明:手机13509427764、18996022706
重庆市潼南县疾控中心袁乃良:手机13389653001
重庆市潼南县疾控中心王奕锦:手机18996022717
重庆市潼南县疾控中心唐述先:手机18996020760
唐述先伙同财务科科长冯桂华:手机18996022696
其中袁乃良、唐述先、王奕锦、冯桂华、王浩是罪魁亏祸首。
English Version: https://en.minghui.org/html/articles/2012/1/9/13059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