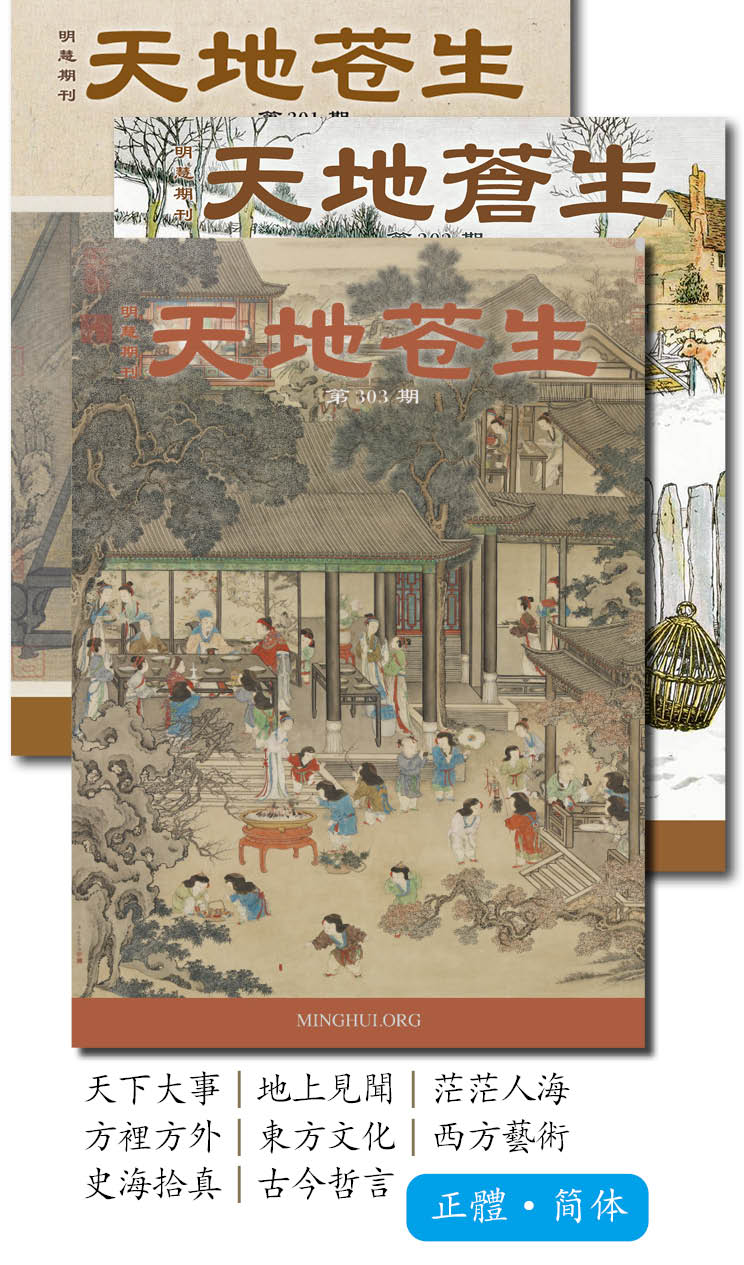四川仁寿县大法弟子黄昌东被迫害经历
题记
我叫黄昌东,四川仁寿县大法弟子。一九九五年八月二十六日,我在仁寿县某书摊请回《中国法轮功(修订本)》,当天傍晚,我到家后一口气就看了近一小时。我惊讶发现,我自高中以来所患的神经衰弱症立马消失遁形了!因为这之前两年中,我看书一、二十分钟就头痛、疲倦的不行,非躺下睡两个小时不可。这本书中,大法师父把道理说的很透彻明白,我便开始看书自学。一九九五年十月份,我又在成都市龙池书市请回《转法轮》一书。在学炼法轮大法以后,我多年来的慢性鼻炎、盗汗、易感冒的症状不知不觉中很快就好了。高中毕业后因家境贫寒而未能上大学的压抑和不满的情绪,也在大法师父的启悟下平衡下来。
刚看大法书后,我还出现一个明显现象:我口中、心中常常哼着自享其乐的流行歌曲(包括色情的东西)嘎然而止,我发自内心的感到那些歌词出不了口,太脏了。这自然源自于法轮功重德向善,更是师父纯正、慈悲、祥和的能量场所致。“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我发自内心这样认为。同时在不断学法中,我明显发现到自己身心巨变,也知道与大法更高标准的要求还差远去了!师父教我们从做好人做起,做更好的人,更更好的人,最后完全是为着别人的人。
但由于自己某些执著心没及时放下,由此而造成人心难断与感情的纠葛,被共产邪灵利用而给自己修炼带来严重干扰。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以来,我两次被非法劳教,被多次传唤、拘留,更多次被派出所强闯住宅、骚扰、抄家、搜身。
下文从揭露迫害的角度,回忆自己的切身经历,但愿能唤醒世人的良知善念。
一、邪恶的洗脑
一九九九年十月下旬,仁寿县公安局一科科长胡显文亲自到汪洋区大洪乡坐镇执行上级的荒谬指示,哄骗我写不炼功保证;一个李姓警察对我又跳又闹,大有大打出手之势。我坦然的告诉他们法轮大法使我身心受益,道德回升。他们竟不顾百姓疾苦,反而把我列为重点迫害对象。之后, 派出所李科祥(所长)指使代成名(指导员)非法拘留我三天。以后,一旦上面有点风吹草动,他们就强迫我到派出所去问这问那,关押一、两天,成了“家常便饭”。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二零零三年九月,我先后两次被非法关押在仁寿县看守所。犯人强迫我背监规,所长周建国、指导员郑本强还亲自抽我背
二零零一年一月至九月初,我被非法关押在峨边沙坪劳教所,强迫我背《劳教人员守则》。二零零一年一月底到集训中队,我被强迫当众领读《劳教人员守则》、《劳教人员日常行为规范》、《劳教人员日常生活规范》、《集训严格劳教人员规范》,约每周一次。还有每天下午的一次约几十分钟在舍房内被强迫读美化吹嘘中共恶党的所谓政治思想读物。
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下旬,我被非法送往绵阳新华劳教所。劳教人员张建军、宋能等强迫我背所谓的“所规队纪”,备受人格上凌辱!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绵阳新华劳教所朴静管教利用我求出去的心,诱骗我写了模棱两可的“三书”(保证书、悔过书、决裂书)。我心里想这是应付邪党劳教所的,但其实我已经开始上当受骗了。之后,我在劳教所的安排下,还向大法弟子田旭、严华云、吴天从、吴兴东、张德元等人暗示过此邪悟;所幸的是他们都否定了我当时的邪悟,免于我在劳教所被欺骗的自毁、毁人中造下更大的罪恶。
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汪洋镇委副书记吴连波、政法委书记王学轩、综治办张思德(可能是此名)、汪洋派出所指导员周勇四人非法将我从家中拖上警车,送到仁寿县天梯某农家乐办所谓“学习班”,实质就是洗脑班,强制我看中共邪党歪曲事实的光碟。
我被关押的当天晚上约九点钟,突然雷声震天响,响雷很低,就象打在我被关押的那间屋的窗户上,天公大有轰雷击毁这非法限制大法弟子人身自由之地的势头。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惊雷示警,县政法委书记杨军虽心有余悸但仍在为他自己所参与的迫害大法弟子的罪恶行径狡辩,他说:“前几天就关了几个炼法轮功的进来,唯独你刚被关进来就出现这种异象,这还证明不了我们把法轮功炼习者集中到这儿来‘学习’是错的。”
直接参与这次犯罪活动的机构是眉山市“六一零”的人员、有自称是眉山市人大的王某(女、四十岁左右)、徐某(男、三十岁左右)、眉山“六一零”主任何某、主任蔡某、书记刘某、仁寿县文林镇派出所(在仁寿“天梯”附近“巡逻”)、汪洋镇政府蒋忠等人。他们强迫大法弟子看诽谤师父、诽谤大法的光碟,逼迫写所谓“三书”。自称王姐的眉山市人大王某还假惺惺的对我在绵阳新华劳教所的情况问长问短,并企图向我兜售某某在绵阳新华劳教所“转化”的如何好,现在工作安置的如何如何好。她见我没说啥,进一步诱惑我说:“你看你两次被劳教,脚腿被打的不能行走,──看来你师父根本就没管过你,还是要相信政府才能帮你”。我脱口而出:“如果没有师父保护,我已经被整死过几次了!”我放开声量重说了几次,我被他们压抑太久,喊出了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在场所有人的眼眶都湿润了。
几天后,我被迫采用了玩文字游戏的方式,包括他们叫仁寿电视台给我录了像,自己心里虽觉不对劲,但仍想,在这特殊的场合下,该明白的人就明白,实在不明白或心里明知是迫害法轮功而为着利益把良心出卖给中共的人,要选择与大法为敌而自毁前程,那我也只好随他去好了,一句话,还是自己的善心不够,无形中障碍了自己在任何环境下堂堂正正讲真相,从而让世人明白中共恶党之邪恶。错过一次向所接触的善念尚存的人讲真相的机会。
二、第一次被非法劳教 惨遭肉体折磨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一日上午十一点左右,我正在汪洋镇富民街下段拉人力三轮车,派出所指导员代成名骑摩托车把我骗到派出所,强迫我写字,看我笔迹。我从他们的问话中探知,由于仁寿县禄加区天娥乡邮递员的检举,从邮箱中发现了我邮寄的真相信件,其人见有揭露小丑江××的内容,兴奋的认为这是邀功请赏的大好时机,好象还把这事直接报告到省公安厅。
下午,派出所警察非法抄家,搜走了我的大法书籍,师父法像、香炉和十几张还没有发完的真相材料;协警员李云学为能“满载而归”高兴不已,他自夸只要他去了的地方保证搜出东西来,派出所其他人都不中用,而奖金还得和几人均摊,他发牢骚说自己为共产邪党效劳,忠心耿耿却“怀才不遇”。他被共产邪灵利用的理智不清,语无伦次,而意欲发泄到我身上,他吓唬我说:“不说清楚,今晚我来收拾你,把衣服脱光,象共产党原来整那些人一样,挂上绳子吊起来打!”
当天晚上,我被送往仁寿拘留所。第二天下午,被关押进看守所。直接参与此侵犯人权之事的人有:汪洋派出所李科祥、代成名、欧春雨;仁寿县公安局一科科长胡显文、眉山市公安处王支队长、谢警官等。
在看守所,我被强迫劳役,做鞭炮,被牢头狱霸周伟强迫用布擦地板,为他洗衣服。宋强、刘利、李冰等一些犯人由于受恶党的毒害宣传,对我进行毒打,他们把打人的方式分为“穿心莲”(用拳打胸部),“贝母鸡”(用肘击背部),站三角桩(头部和两脚三点触地)等等。有几次我被打的回不过气来,他们还开心的说这是“死亡游戏”,我感到气憋的难受极了,请师父帮助,约十多秒钟后才回过气来。
一次看守所所长周建国知道我在里面炼功,他把我调到关押死刑犯李勇军的监舍内,李勇军强迫我双手向上伸直,长时间站立,我不配合,把手变成“头顶抱轮”或“两侧抱轮”的姿势。他就叫一个绰号叫“梁疯子”的犯人(富加区人氏)和另一犯人对我前胸后背同时重击,还发狂得意的说,这叫“日月穿心莲”。他们还强行把燃着的烟头塞进我口中,叫我含熄,并逼迫我吞下肚去。
被非法判劳教后,我转入二十仓,犯人杨建(可能是此名)用木制模框(做鞭炮的)猛的击在我的右眼和鼻根处,顿时眼皮肿了,眼球内起了血点,鼻血往出淌。杨建见此情景,怕承担责任,自己也吓得要去报警察。我说自己是大法弟子,没事。有人说他是“恶人先告状”,他说我炼法轮功在先,他只不过是为自己推卸责任而已。
二零零一年一月五日,仁寿县公安局见我思想“顽固”,把我送到峨边县沙坪劳教所单独关押。被送到峨边入所队(二中队)的当天,天阴沉沉的,山上雪花纷飞,入所队大门前一片阴风,仿佛曾有几多被中共邪党残害致死的冤魂在争相述说:这不是好人应该来的地方!所有门岗(劳教人员)和几个迎面跑来的教头、教霸当着警察的面,高声尖叫“打死!打死!”,并马上安排搜身、剃光头,并强迫站军姿几小时。当晚,室长余巴伦(教头)就挥我几个半握拳打在脸上,他还说这是这儿的“见面礼”,洗脸帕被他们偷去擦地。(约半年后,家里寄来几十元钱,我才有了洗脸帕。)
五天后,我被转入五中队二组,组长叶建如,张某指使“打手”半握拳打我脸,罚弯腰、手指触地、直腿十多分钟,强迫我打电话或写信回家叫寄钱来,并说这里是用钱买好过,说这里值班带组的都是用钱买的,所以享有泡着茶水、翘着二郎腿靠在椅子上“改造”的权利。(这种现象在仁寿县看守所、绵阳新华劳教所也普遍存在,只是做的更加隐蔽圆滑而已)。他们开口就要五六百,八百,一千;张某还当场把另一人寄来的一百元人民币烧了,狂跳着说:这点钱有啥用。我写信叫家人寄几十元钱来买生活用品、牙膏、洗脸帕、卫生纸;他们就把我的信撕了,对我拳脚相加,并罚我用脏布帕去擦凹凸不平、满是泥尘的水泥地。
由于我坚持法轮大法信仰,十多天后,我被关到集训中队迫害。我因为坚持法轮功信仰、告诉别人法轮大法是好的,常被教霸指使人给我半握拳,我的脸常是肿的,额上被犯人用手指弹起了包。有几次我被打的倒地上十多秒钟后才回过气来。他们还羞辱我,天天让我提马桶倒屎倒尿。就连我九月八日解教离开的前一天晚上,教霸肖勇竟用拖鞋底猛打我的脸,被打的肿了很高。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我正在汪洋镇围城路与广场街交界处蹬人力三轮车,代成名与派出所另一警察开一辆面包车来叫我马上把车停那儿,跟他们一起去派出所走一趟,我坚决不配合他们的所谓要求、命令和指使,他与另一警察便强拽我上车,我坚决不从,代成名拽着我的头发往派出所拖,口中还叫不停的叫骂:“你头上赖毛就少,再不去头发掉光了可别怪我!”
三、第二次被非法劳教 被迫害致不能自理
二零零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在汪洋镇方正中学某老师举报下,仁寿县教育局施压,汪洋区副书记(可能是主管政法的)黄世国(此人于二零零五年遭恶报遇车祸当场死亡)指使派出所代成名等人强行抓我到仁寿看守所。
第二天早晨八点过,所长周建国叫我出监舍站在院内中间的空地上,他问我还炼不炼法轮功,我告诉他法轮大法好。他再追问炼不炼,我说“炼”;并向他讲述大法使我身心受益,大法是被冤枉的。他冷笑着说:“好,那你炼给我看,看你敢不敢炼?”我心里想来了就是证实法来了,便开始炼第一套功法,他叫了两个所内服刑人员左右一人各持一棍,强迫将我两腿叉开“大”字型站着,我开始发正念,并放开嗓门,高呼“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周建国忙跑回来叫犯人来捂我的嘴,打我,乱踢我,还有几个警察,他们见制止不了我的喊声,骂犯人不中用,急忙去找小木棍横塞我的嘴,用铁丝从头后拴好固定。并叫八个犯人、警察把我抬到刑床上,四肢用铁丝和手铐固定,吃饭、大小便都不松开,一直将我捆绑在刑床上九天九夜。当时是秋天,加之看守所内更是阴森风凉,刑床上没有垫更没有被子盖。只有一、两个晚上个别值夜班的在押人员实在看不过意,私自给我盖上被子,还说这是冒着被牢头、警察看到后会受处罚的危险。
期间,我多次要求看守所警察放我下来,但得到的回答是:没有所长周建国的允许,他们没权放。后来,我在新华劳教所才听一同修说刑床是看守所早已禁用的刑具,是严重侵犯人权的恶性事件!整整九天九夜,我被强行固定在刑床上苦苦煎熬,还要遭受犯人的打骂,一次,一个十几岁的被牢头等人唤作小幺儿的在押人员竟然用洗澡帕手淫后直接将脏毛巾当众捂住我的被打、抓伤并肿痛的脸和嘴唇处羞辱我!当我指问他时,他还拿来打地帕猛擦我的脸部,疼的我脸、嘴部肌肉和骨头都火辣辣的,他们还得意的狂笑:我给你干洗脸!
二零零三年十一月十三日,我被送往绵阳市新华劳教所,看守所警察李某、杨某去办交接手续,因没有我被非法劳教的所谓决定书,黑窝新华劳教所拒收,我当天被送回。看守所警察何某等人过来暴打我一顿,他们怀疑是我把他们的黑材料吃了。他们气急败坏的说:这是自仁寿看守所建所以来,第一次送走而被退回了的人,这怎么可能?我告诉他们大法弟子是好人,法轮大法好,苍天有眼,这是在警醒你们啊!立即释放大法弟子吧,不要做出令天地震怒之事!
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看守所周建国自己出马,强行将我劫持到绵阳新华劳教所。下车后,在大门外往高墙内一望,似乎有许多黑色的奇形怪状的东西在上空怪叫,透出阴森恐怖的气氛,进了劳教所大门,周建国才在别人的提醒下给我开了约七斤重的脚镣、手铐。由于戴了一个多月的镣,刚取下的几十步,我走路都稳不住。我被非法关押在六大队三中队。
被送进六大队三中队,正是中午快十二点了,一些所谓的“帮教”人员(其实是劳教人员),轮番或几人同时来用他们受中共邪党所编造的谎言来欺骗我,被我一一否定了,我向他们讲真相,一直到下午,他们感到企图“转化”我从而捞取劳教所减期的希望非常渺茫。到操场上,他们歇斯底里的叫我站军姿,不准我面朝人群及其他法轮功学员,他们说我一副和尚像,会影响别的人,影响这里的改造秩序。我想这主要源自于大法中的正念,让邪恶害怕胆寒,因为我站军姿时或站或行时,都在发正念或背法。
之后,我被单独关押在邪恶所谓的超级严管室,三个包夹(劳教人员)对我进行所谓“帮教”迫害,有张建军、重庆崽儿(别人这样叫他),还有一个劳教人员组长。约一、两个星期后,包夹、帮教劳教人员增至八人,很多都忘了姓名,有一个较邪恶的包夹叫宋能,约二十岁,乐山市沐川人,记的比较清楚些,他因为我拒绝“转化”,就找借口说纠正我军姿对我脊背和腰部猛击,我几次痛的跌下凳子,宋能还怒目相向,对我的平和慈善的目光,他马上就显出心虚与恐惧,以借口纠正我姿势为由,叫我目光转为平视前方,他歇斯底里的说:“你还想“转化”我么?不许看着我,我是恶人!”
我被单独关押的一个多月里,每天早晨六点起床,中午不准午休,晚上十点钟其他人睡觉了,我还要一个人坐到十二点。
二零零三年腊月末,一天晚上在洗漱室,一法轮功同修问我是,哪里人,我告诉他是仁寿人,又问他,他也告诉了我。就这简短的一问一答,包夹张建军将此事告到了中队,因为本来就没事,中队没表态。民管会(由班组长劳教组成的)为了讨好上级,还叫包夹张建军和另一包夹去尾岗晚上标半小时军姿,后来听包夹说他们只不过去坐着休息而已,因为跟民管会是朋友,但张建军却以此为借口把我盯的更严了。
二零零四年二月九日,我被转入六大队二中队,二月十三日,中队开邪恶的揭批会,大法学员被“一包一”或者“二包一”(两个包夹一个大法弟子)带入教室,所部教育科一个牛高马大、满脸横肉的恶警,拎着录音机放诽谤大法的录音,接着邪悟者走上台念中共邪党强迫其抄写的那一套套诽谤的陈词滥调。我心中难受极了,我不停的发正念,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并清除干扰在场人的破坏大法的邪恶因素。
场上的空气异常的紧张,护卫队在教室外提着电棍巡逻,这时,在我前排的李永弘站起来说:“你们不能这样”“法轮大法好!”随即被包夹摁翻在地,护卫队迅速赶到,叫包夹捂住嘴拖了出去。之后,刘永生、吕同修(乐山市沐川县司法局副局长)又站起来制止劳教所行恶,但都被拖出去了。
这时场上的空气越来越紧张,自李永弘站起来后,包夹王和平和余建勇坐在我左右两侧异常紧张,他们急忙用手来捂我嘴,我正念制止他们,我能感到他俩的手在发抖。我努力使自己镇定下来,但有一股能量冲我嘴唇上下不由自主的在动,包夹及护卫队紧盯着我,我尽力使自己再镇定下来,因为我意识到此刻只要稍一声张,声音还没出来就可能出现前几位那种被干扰的现象。
我发正念除恶,台上的邪悟者声音越来越小,越来越弱,而这时包夹和其他人已没有注意我了,我便大呼一声“法轮大法好!”并用正念把这句话打入在场所有人的耳内心中,以唤醒在邪恶的高压下被迷惑后强制洗脑的众生,激励同修的意志。在场的人似乎被震住了,空气似乎凝滞了,包夹王和平、余建勇及值班教霸、护卫队回过神来后,把我摁翻在地,捂住嘴,抬起来,从教室后门出去。经走廊、办公室到大会议室,他们放我在地上,用事先准备好的脏被盖把我蒙上盖住,一阵狂打乱踢之后,护卫队将我手反背身后上绳子,包夹张建军一边踢一边打一边主动帮护卫队紧绳子,嘴里还不停的叨咕叫嚷:“早就想狠整你一顿了!上紧点,这人太顽固!”之后,我被拖到走廊上,中队长付卫东走来用电棍电我嘴,并一脚直踢我的腹部,一时回不过气来,身子不由往下坠,两边包夹强架起我,还嚷:“装死!”
我被带到办公室,护卫队有个人还说:这是上次第一回送新华因没档案拒收,公开在劳教所大门外停车旁炼法轮功的。我当时就想冲过来狠整你一顿!王和平还当着护卫队的面狠狠给我脸上疯狂打耳光,打累了,他还吐我口水。
在这次揭批会上自发参与讲真相行使自己言论自由权利的还有大法弟子王仁伟(被包夹、恶警打肿右眼,眼球红肿,内有血点,一个月后解教时都未散)、魏浪等。
当天中午,我绝食抗议,被强迫戴摩托车头盔约一周,每天二十四小时不准取。次日起床时,我发现自己怎么也爬不起来,腰、胸、腹部剧痛,我费力的用两只手抓住床沿,请师父帮助。我左手稳住床沿不动,右手从右侧床沿开始,缓缓从身后划弧线至脊背正中,再上身向左慢慢侧身,靠右手慢慢的把腰抻起来。
自绝食那天起,中队几乎所有管教轮番找我谈话,他们是管教李某、邓某、朴静、付卫东、何学林;还有大队长黄明、副大队长杨某。
三天后,二月十七日上午,我被骗下楼做体检;下午我被强行灌食,有包夹八人强抬我到手术台上,我坚决制止,有包夹猛击我胸部(一个外号叫“对对眼”的人),还有包夹猛击我腹部,杨建还猛捏我脚和小腿,口中念念有词,好象是说他在西藏学来的邪术(他是生活在甘孜州的汉人)。他似乎说凡是他整过的人脚筋就断了,从此不能走路。他们折腾了二、三十分钟也掰不开我的嘴。何学林找来钢丝钳妄图剪掉我的门牙。何学林说他有的是办法。之后,他们往我鼻孔插软管,呛的我直打喷嚏,他们趁我呛的张嘴之际,把从鼻入口的软管从口中绕了出来,便用事先准备好的他们所说的“牛奶”(其实是里边有药物的奶白色液体)开始灌。参与此次野蛮灌食的有:副所长赵泽勇、中队长付卫东、何学林,管教张小刚,朴静,护卫队警察两人,包夹黄良平、杨建,米进海(后遭恶报病危出所)等八人。还有内部医院的廖医生(男,五十多岁),米兰(女,三十多岁),医院院长等人。
之后,我被关进十八监舍单独“超级严管”约一个星期,这次还被延教两个月──仅仅因为说了一句真话,行使了作为公民的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权利,就惨遭共产恶党的新华劳教所的残酷镇压。
由此可见中共的政策乃至政权不合法,他自己也明知不合法,是自欺欺人的,所以才对老百姓的和平言论及鸣冤如此高度惊慌与小题大做而大动干戈。
二零零四年四月二十六日凌晨,我早起打坐。值班劳教人员过来制止,报告中岗,中岗再报当日值班管教张小刚(新华劳教所戒备森严,铁门处是门岗,走廊上是中岗,厕所处是尾岗,各寝室每天晚上有一人面向室内值夜岗,有人笑话说是天安门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影射)。我拒不放下腿,他们把我抬起并拖到办公室,中队长何学林和中岗朱涛等人暴打我一顿,何学林的皮鞋都踢烂了,朱涛表现的特别卖力,后来自称是来劳教所打的最过瘾的一次。他们还狂笑我脸上成了熊猫。晚上,沈锐管教值夜班时,强制不许我上厕所,除非写“三书”,他还罚我蹲军姿,并在我头上跨过,狂笑着:“看你能不能受胯下之辱,出去告我吧!吐你几泡口水!”
何学林让我在所谓的笔录上按手印,我拒绝,他看了包夹王和平、罗红光等几人一眼就关门出了民管会活动室。王罗“包夹很快会意,强拖住我手指,按进印泥盒,取出后,再将写有我名字的纸拿过来在我拇指上一接触,印上手印,由此可见中共邪党是如何的强奸民意的。为此事我又被延教二十天。
二零零五年六月,劳教所强迫法轮功学员由包夹带到教室看诽谤、污蔑师父的“遭殃电视台焦点谎谈”的光碟,然后回到寝室写所谓的体会。我坐在教室凳子上发正念,在包夹不注意时,我迅速坐在地板上双盘我立掌,并呼喊:“法轮大法好!”我被拥上的数个包夹打翻在地,捂上嘴,抬出教室,经走廊到大会议室。管教沈锐要给我穿上“马甲”挂起来,被我正念制止。管教朴静走来叫他们让开,他用电棍电我,并用一种特制的钢质圆圈框打我脸,嘴、鼻等部位,并骂道:“我早就料到你要乱来了,这是新年玩具,我专门找来留这儿收拾你的。”之后,中队长何源督阵,叫张小钢给我戴上摩托车头盔,长约十天,单独关押,这次可不比上次二月份戴头盔,现在是大热天,二十四小时不取,头发汗湿得臭得自己闻着都发呕!劳教人员(民管会主任)戴军、组长赵跃,包夹雷小钟、木建铃、贺建二十四小时看守,铺在地板上睡,他们还强制我在比膝盖还矮一半的小凳子上坐军姿,从早上五点起床,一直到凌晨两三点才准睡觉。戴军叫嚣:“不打你,不骂你,所规队纪约束你,发一个矮板凳坐死你!”
我坚决不配合,戴军就指使贺建用脚踩我脚背脚尖,用脚猛跺,几百次发疯发狂的跺脚,戴军看贺建累了,他又接着跺。直接致使我脚、下肢无力(一个月后更明显),部份知觉丧失,被送医院检查,医生用物体击打我膝部,发现我小腿纹丝不动,失去正常的条件反射功能,不能行走,丧失生活自理能力,接下来手也直不起来,近于偏瘫。八月下旬,我被强行送进劳教所医院住院部,临解教(九月九日)都未见丝毫好转,医生也说没办法了,无法保证我的四肢能治好。
四、恶毒的经济迫害
劳教所通知派出所九月十日来接我回家,送至离我家最近的公路旁下车,我手扶车门,慢慢下来,年近六十三岁的父亲背我回家,五岁的儿子幼稚的拿着电瓶动作敏捷的走在前面照亮,不时的回过头来看背着爸爸的爷爷。来到院坝,母亲搬来椅子让我坐下。抬头望天,看天上满天星星特别多,特别亮。父母亲也说这几天晚上,特别今天晚上星星特别多,特别亮。我无限感慨,被关押约两年(七百余天)后,现在回到家才看见这满天的星斗。
回家后,我生活不能自理,自己洗不了脸,走不了路,手扶墙可挪动几步,稍不注意膝一曲就跌坐在地上,两手端碗拿筷子都相当难,双手结印手指是合拢的,成不了椭圆,我就用毛巾捏成团塞在两手拇指与四指间支起无力的手呈椭圆状。单手立掌是倒的,我就坐在门边,手放在门面上。莲花手印手指要合拢,我就用一只小饭碗,碗口朝上放在两手十指间,动功一、四套功法因有屈膝动作,做不了,我就僵直着腿先炼二、三套功法,但常常一不小心就跌坐身后椅子上。
在劳教所医院及绵阳市某医院都没有把握治好,而接我的人建议我再到县医院检查检查。而当地不明真相而很可能被地方政府煽动的人在街头、车上碰着我父亲问:听说你儿子患了“肝癌”!四川话“肝癌”与“干挨”同音,意指我白白挨共产恶党的整而有冤无处申。当然,这也可能是激我们要追究迫害者的责任到底。
自从上文提及的一九九九年十月后我被限制在本地派出所辖区内,由于找不到工作,被迫在小镇上靠蹬人力客运三轮车维持生计,小镇上有几百辆三轮车,每天辛辛苦苦挣一、二十元钱。就这样艰难的维持着生活,即便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派出所代成名、唐雪峰还先后两次在我营业途中强行带到派出所并被劳教两次,长达近三年。随时以所谓的传唤名义到派出所去问这问那的次数不下几十次。
二零零二年九月下旬,邪党十六大前夕,我在成都东光小区送水,县政法委杨军、县公安局邓柏松(已遭恶报死于癌症)、汪洋派出所警察代成名威逼利诱,胁迫肖碧春引路,带来两辆警车,一个蒋姓警察(蒋三)竟掏出手枪强行带我到仁寿戒毒所非法关押十多天。之后不久,蒋遭恶报被人打伤,鼻子正中山根处敷上纱布挂了彩。
二零零三年初,我到成都打工,警察代成名到我家骚扰,恐吓我年迈的父亲,逼他叫我回家,不能在外地打工。派出所以限制民众的信仰、言论自由为借口,强行破坏民众的生产、生活,这种执法犯法的罪恶行径,不是他们声称“执行任务”所能推卸的了的。这恐怕也只有在这个“党大于法”、“权大于法”的专制、独裁、极权的恐怖主义中共邪党国家才存在。
另:一九九九年十一月,汪洋派出所警察罗尚彬,扣押我妻子肖碧春川绵厂工资约千余元,派出所还和川绵一厂相互勾结,强迫肖碧春辞工,从此肖失业至二零零三年,造成经济损失至少两万多元。
汪洋派出所警察至少不下于十次非法到我家非法抄家,把衣服、被子等用品满地乱扔,抄走了我的大法书籍等物件,就连从商店买来的香炉,坐垫都被拿走了。协警员李云学还常叨着一句话:“看看有没有值钱的东西!”而他们看到的只有一台十四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几间土筑瓦盖和一间砖砌瓦盖的八十年代初的老式房屋,似乎在述说着中共恶党独裁专制下普通民众的清贫生活。派出所警察还经常歇斯底里的叫嚣:“你们再炼,我们把你房子车一转!”只有明白的人悄声问我:“听说那天鬼子又进村了!”
每当恶警、村镇邪党官员要闯到我家的头一天晚上,我几乎都要做同一个梦:一群手执破罐烂碗的疯癫、孤、寡老人或叫花子来我家门前乞讨。由此,我悟到他们虽然逞凶一时,如不悬崖勒马,弥补过错,必然天理不容、折福损寿!甚者业大销毁!
迫害的相关人员、单位(区号:0833):
姓名 单位 职务 邮编
胡显文 仁寿县公安局一科 教导员 620560
杨军 仁寿县政府 政法委书记 620560
周建国 仁寿县看守所 所长 620560
李科祥 仁寿县汪洋区派出所 所长 620587
王学轩 仁寿县汪洋镇 政法委书记 620587
代成名 仁寿县清水镇派出所 所长 620560
赵泽勇 绵阳新华劳教所 副所长 621000
何学宁 绵阳新华劳教所 六大队二中队中队长 621000
付卫东 原绵阳新华劳教所 六大队二中队中队长 621000
沈锐 绵阳新华劳教所 六大队二中队管教 621000
朴静 绵阳新华劳教所 六大队二中队管教 621000
张小刚 绵阳新华劳教所 六大队二中队管教 621000
周建康 仁寿县汪洋镇(路段车辆)收费处(可能是此地址)620587
何源 绵阳新华劳教所 六大队二中队中队长 621000
欧春雨 仁寿县汪洋区派出所警察 6205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