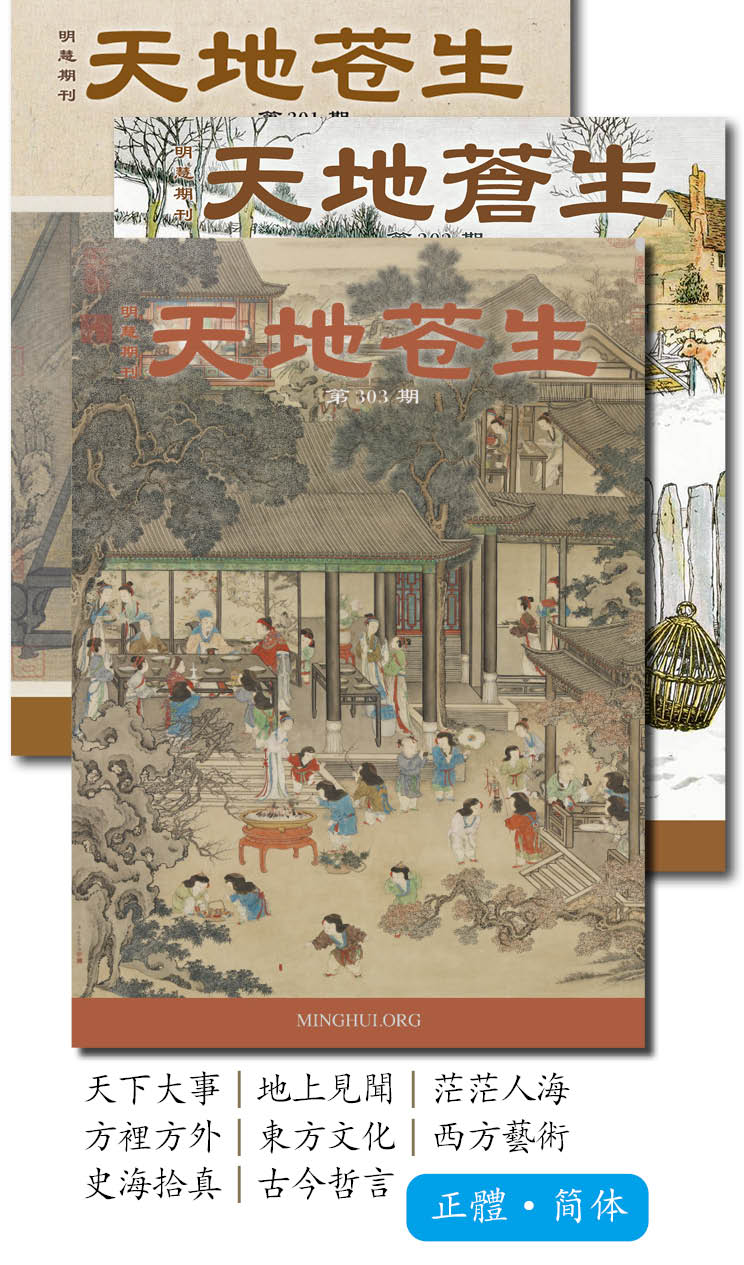遭五年冤狱 浙江大学副教授控告江泽民
一九九九年六月十日,在江泽民的个人意志和淫威下,中国大陆成立了凌驾于国家宪法和法律之上的全国性恐怖组织──纳粹盖世太保似的“610办公室”,并在同年七月二十日之后,命令“610办公室”系统性的对坚持信仰“真善忍”的中国法轮功学员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杀”的灭绝政策。潘开祥所遭受到的一系列迫害,都是在“610办公室”直接指使下进行的。
潘开祥说:“被迫害后,工作失去了,收入也没有了。这样,给自己和整个家庭造成了很大的经济上的困难。出狱后,多次去找工作,因为对法轮功的信仰及被坐牢的经历,很多单位不敢要我。最后去了朋友介绍的一个卖墙纸的公司,当时一个月只有八百元的工资。后来,自己开了一个卖墙纸的个体商行,生意也不是很好。在这期间被绑架至洗脑班迫害,由于长时间无法经营生意,也严重影响了自己的生意。”
以下为潘开祥陈述他遭受到的迫害事实:
(一)无数次被骚扰,传唤和非法对待
我于一九九六年初开始修炼法轮功。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始,中共警察和特务就开始了对法轮功修炼者的秘密监视。我当时是中国一所著名大学(浙江大学)心理学系的副教授,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我成为他们监视的重点对象,电话被监听,行踪被监视。在四月二十五日至七月二十日之间的某一天,我正好在原学校(浙江大学西溪校区)附近八字桥炼功点晨炼,当时打坐时,我把自己的一个放着很多个人物品及法轮功书籍的皮包放在旁边,当打坐完后,发现自己的包不见了。后来,我看到了西湖区公安分局警察朱晓明手中在拿着我的一本法轮功书籍。原来,他们为了监视我,把我的个人皮包给偷拿去了。这是非法占有一个公民的私人财产的开始。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开始,中共江泽民集团出于个人的妒嫉心,发动了对法轮功精神信仰群体的丧失病狂的迫害,一时铺天盖地的污蔑法轮功的谎言充斥所有的电视广播报纸等。其实,即使在中国,修炼法轮功也是合法的,更何况这种精神信仰已经带给整个社会巨大的正面作用。
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违反国家的法律,践踏了人的尊严,侵犯了人的权利,犯下反人类罪,酷刑罪等。在中共漫天的污蔑宣传中,使不明真相的民众对法轮功及其修炼者产生了强烈的敌视和愤怒情绪,“610办公室”人员,学校单位领导,社区相关领导,公安局政保科的警察等借机捞取政治资本,给法轮功修炼者及其家庭施加巨大压力,企图让法轮功修炼者放弃精神信仰。这么多年来,他们不断的骚扰我们,或非法传唤我们,或私自闯入我的家里,或对我们软硬兼施,威逼利诱,甚至对我的亲人,包括我的妻子、儿子、岳父岳母施加压力,叫我放弃对法轮功的精神信仰。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我们得知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的消息,去浙江省人民政府信访办上访。结果被学校的保卫部门强行绑架回学校,限制人身自由,并强行收看中共江泽民集团开始镇压法轮功的消息。学校领导要求我放弃法轮功修炼。当天位于教工路一号的家里被警察抄家,要求上缴法轮功的所有资料。很多警察强行抄走了很多大法资料。
一九九九年九月五日,本人与其他法轮功学员在杭州市西湖区龙井村喝茶聊天,被认定为“非法聚会”,事后被杭州西湖区公安分局警察传唤,并强迫要求交待本该正常的公民的活动。传唤没有时间规定,当提出要求出示合法的手续时,到最后才补给我一份了事。如果超出了传唤规定的时间,也随意延长时间。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四日,本人与其他法轮功学员在杭州植物园聚会交流法轮功修炼心得。事后去学员陈廷卫家中聊天。这些也都被认定为“非法聚会”,同样被强行传唤,交待一个公民正常的活动。
从迫害开始到我第一次被捕送进看守所,以及第一次被捕到第二次被捕期间,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区公安分局多次传唤并骚扰我的正常生活,有时深夜才能回家,更残酷的是想罗列一些所谓的罪名,好给我施加压力,以便使我放弃我的精神信仰。
二零零五年十月二十二日,我在监狱里被迫害五年后,回到家中。原以为生活能够平静。但实际上,在共产专制的国家里,整个社会就是一个大监狱。在我出狱后的时间里,杭州西湖公安分局国保大队,伙同杭州西湖区华星社区,经常借关心生活为名,了解我的思想动态,暗地里监视,并监听我的电话。在节假日和一些所谓的敏感日,来我家骚扰,或强行叫我们去社区接受思想汇报,并给我施加压力以便我放弃对法轮功的信仰。
他们在了解到我仍然在信仰法轮功,就千方百计的给我和家庭施加压力。并运用黑社会恐怖方式绑架我两次,被强行秘密送进黑监狱——洗脑班。有一次,也就是我被第一次绑架到洗脑班的前夕,杭州西湖公安分局古荡派出所警察杨镇,华星社区书记沈国坚到我上班的单位,杭州西湖区综治办翁广禹态度极其凶恶的说,要我放弃对法轮功的信仰,否则要送我去洗脑班。
(二)二次被非法抓捕,被非法判刑五年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被杭州市公安分局非法抓捕,关押于杭州市西湖区看守所,至二零零零年六月五日被释放。这是第一次因信仰法轮功被非法抓捕和关押。
在看守所被关押期间,在杭州市“610”的指使下,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区公安分局,浙江大学保卫处等把我作为迫害的重点对象。甚至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张德江亲自批示,以使达到转化我和放弃对法轮功信仰的目的。当时被关押在看守所一间阴暗潮湿且终日见不到阳光的房间里,十几个人,多时达到二十几人被挤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晚上睡觉时,不得不侧着身子才能勉强躺下。从上午七时到晚上七时强迫进行高强度的劳动。如果完成不了规定的任务,就会受到监房里牢头的惩罚,或罚冷水浇头,或罚长时间蹲立。经常加班到晚上十一时左右。吃的是霉变的米饭且吃不饱。晚上睡觉寒冷难忍。并且规定一天上厕所只能在几个时间点上才能进行。
在这期间,中共不法人员们多次提审我,网罗众多罪名,以便促使我放弃对法轮功的精神信仰。二零零零年四月十五日至六月五日,他们为了达到转化我的目的,由浙江大学保卫处出面,把我监视居住在浙江大学求是新村的一间宿舍里,限制我的自由,并且两人日夜二十四小时监管我,逼迫我违心放弃对法轮功的信仰。
二零零零年六月五日回到家后,身体和精神受到巨大的创伤。三十几岁的人,头发已大面积脱落,脸色变得苍老,精神和灵魂受到强力的伤害,晚上睡觉时,经常梦见自己赤身裸体在洒满玻璃碎片的地面上打滚,异常痛苦。
二零零一年一月十六日,西湖区公安分局朱晓明,谢良冲进我位于杭州市西湖区教工路一号的住处。他们犹如强盗般的冲进来,上下一阵乱翻,抢走了我的很多物品:《转法轮》书一本,《洪吟》一本,SONY软盘一片,《法轮佛法 悉尼法会讲法》二本,《法轮大法义解》二本,《转法轮-卷二》一本,录音磁带三盘,电脑主机一台,调制解调器一台。一月十七日被西湖公安分局抓捕和关押。后在二零零一年六月十八日被杭州市西湖区法院非法判五年,关押在浙江省第二监狱迫害。至二零零五年十月二十二日刑满释放。
在非法关押期间,特别是在监狱期间,在失去了人身自由的情况下,监狱对我进行了有目的,有计划的系统性的迫害。
1.制定严厉的对法轮功学员的管理制度,限制对我的身心自由。
强制剃光头,穿上囚服,挂上严管的红牌,接受牢中之牢的残酷管理。刚进监狱时,我拒绝穿囚衣和剃光头,拒绝背监规,警察就指使监狱里的犯人通过各种手段惩罚我。或长时间面壁站立,或剥夺吃饭权利或限制上厕所的次数和时间等,手段五花八门。有一次,他们为了达到让我放弃对法轮功的信仰,惩罚坐小矮凳,两眼正视墙上的一个点,不能动,双手放在膝盖上,全身坐正。一天从上午八点坐至晚上十点,其间除了吃饭,只能上午在规定时间点上一次厕所,下午在规定的时间点上一次厕所。这样连续迫害了八天。
在监狱里,专门安排由三个犯人组成的小组,对我进行二十四小时的包夹监管。三个犯人,一个任小组长,一个担任打手,一个负责思想攻占。这些犯人,大都是些重刑犯,为了达到讨好警察和多减刑的目的,往往变本加厉的对我进行迫害。犯人孙华和肖兴水尤为严重。有一次,正好是夏天,天气很热,他们包夹三人,在警察的指使下,专门把我安排到一个只有我们四个人的房间里进行折磨。他们不断用难听的语言谩骂我和骂大法,直到让你喘不了气为止。地上划出一个很小的空间,让我坐在里面,不断的接受他们的污蔑法轮功的洗脑灌输,行动不能越过划出的红色警戒线。一天只给我半小桶水洗漱。在规定时间点上才能先报告被批准后才能上厕所。不能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晚上睡觉时,在你能看到的地方,上铺的下面,房间的墙壁上甚至地上贴上污蔑法轮功及法轮功师父的标语。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处在这三人包夹犯的体罚,言语攻击,谩骂和监视之中。恶徒想尽一切手段企图要我放弃对法轮功的信仰。
在整个监狱迫害过程中,我一直被严管,只能在规定的区域活动,不能与其他未经许可的人交谈,更不允许与其他法轮功学员交往,哪怕是目光的接触。没有休闲娱乐活动时间,除了劳动,就是接受他们的洗脑灌输。晚上睡觉,专门有人值班看管我,记录下我的睡姿,讲了什么梦话,睡眠的过程及时间长短。与家人的会面时间,只能在他们规定的时间点进行,有时甚至被剥夺。
2.强迫接受长时间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企图让我吃不了苦而放弃对法轮功的信仰。
在监狱里,被强迫进行很多高强度的劳动。挖地基搬石头,运土种树,平整土地,装缷铁屑(制作扳手后的边料),手工劳动等。包夹犯经常有意逼迫我进行不停的高强度体力劳动。在挖地基搬石头时,包夹犯孙华,徐建国二人拼命的督促我不停的劳动,不让歇息的时间。当时需要把几百斤重的石块从地里挖出来,然后搬运到车子上运走。由于长时间高强度的如此劳动,腰无法直立。直到现在,还留下后遗症,坐的时间久了,站起来时腰无法直立。
3.长时间的精神折磨以达到对我的精神迫害
没有比长时间的精神折磨更痛苦了。中共监狱对我的迫害,无论限制人身自由,实行严厉管制,高强度长时间的重体力劳动,还是利用对家人的压力和威胁,都是为了达到让我放弃对法轮功的精神信仰。他们有一套完整的精神洗脑和思想折磨的方法和措施。除了劳动,睡觉等必须完成的时间外,其它时间基本上都被用于接受污蔑法轮功的洗脑灌输中,并且要求每天写思想情况汇报。达不到他们的思想要求,接下来的就是更严厉的精神折磨。
警察孙升,经常组织包夹犯以与我讨论法轮功观点为由,实为胡搅蛮缠,强行扭曲人的经常思维,达到控制人的精神的目的。具体是这样做的:他们把我的某一个观点提出来,然后要我列出证据来,以证明我的观点是对的。要一步一步说出来,上一步是怎么得出一下步。整个过程是在三个包夹犯的不断的语言攻击,谩骂,胡搅蛮缠下,用录音机录下来,如果我一时说不出来,或说不全,或说不准确了,他们就拿出录音机中的录音,来否定你的观点。如此强奸人的思想的做法真是荒唐!
在长达几年的失去自由的严厉管制环境中,他们运用环境控制,情绪控制,语言控制,行为控制以达到对人的精神控制。而这恰恰是世界上邪教对人的精神控制方法。我在监狱的这段时光里受到的对待,见证了中共邪教对我的精神信仰的迫害。
(三)两次被绑架,强行送入洗脑班迫害
1.第一次被绑架至洗脑班迫害
大约在二零一一年八月底,西湖区公安分局古荡派出所警察杨镇,华星社区书记沈国坚在杭州市“610”的指使下,到我的工作单位里,威胁我,叫我放弃对法轮功的信仰,否则要送我进洗脑班迫害。
为了躲开他们对我的迫害,我几天呆在家里锁上门不上班,或改变上班时间,或很晚才回家,或坐在亲戚的车子里上下班,或翻墙躲开小区门卫的监视。但还是在一天早晨上班的途中被绑架至洗脑班进行迫害。
那是在二零一一年九月七日上午九点多左右,我与妻子一起去上班。当我们走出家门不远处,杭州市公安局消防大队西湖分队门口,西湖区中级人民法院旁,我突然感到有人在叫我的名字,当我回头时,突然有四、五个不明身份的彪形大汉向我冲扑来,他们动作粗暴的把我抓住,我的包和电脑被摔出,衬衣被撕破,纽扣被撕落,一只鞋子不知去向。我的妻子见状大叫起来,他们中的一个人把她抱住,并捂住她的嘴。然后,他们就把我绑架到一辆面包车上,飞快的驶向一个我也不知道的地方。
在车上,几个绑架人,态度凶恶,强行把我架住,不准我随意移动。后来我知道,这是当地610指使下,把我强行送入洗脑班进行迫害。指挥现场绑架的是杭州市西湖区综治办主任翁广禹。没有任何的法律根据,没有事先告诉你去干什么,到哪里去,呆多长时间。而这一切都是极其邪恶的黑社会行径,比监狱里有过之而无不及。
后来我知道,这次被绑架至洗脑班迫害的地址是:杭州市余杭区塘栖镇龙悦水庄,此地是一个旅游休闲地方,洗脑班设在其中的一幢房子的里面,门口设有保安和工作人员,我就被限制在里面迫害长达近五十天。在一个房间里,由两名包夹人员,二十四小时监视,没有人身自由,活动都得听从他们的安排。每天强迫观看他们安排的污蔑法轮功录像,强迫写心得体会,不符合他们要求的,就会安排很多人轮番的与你进行“谈心、交谈”,或威胁我:“如果这次还不放弃对法轮功的信仰,可能从新再把你送回监狱。”杭州市司法局徐如红威胁我说:“你是杭州仅有的几个没有被转化的人员了,我们对你的打击会更厉害,你何去何从自己想好。”他们甚至安排一天的时间,把我送回到我原来被迫害的浙江省第二监狱里感受被关在里面的法轮功学员被洗脑的情景,试图以此恐吓我,以便逼迫我放弃对法轮功的信仰。
2.第二次被绑架至洗脑班迫害
二零一二年八月九日,我在上班时,被杭州市西湖区公安分局的警察绑架至位于浙江省新昌县的洗脑班,在里面被迫害达五十天左右。在这期间,省“610”头目,浙江省第二监狱的一位姓常的警察(在此监狱被迫害时曾监管过我的一位警察)亲自到洗脑班,给我施加压力,叫我放弃对法轮功的信仰。每天,很多包夹人员轮番对我进行思想攻心,逼迫我放弃对法轮功的信仰。
(四)在生活上,经济上,工作上对我的严重迫害
中共对我法轮功信仰的迫害,使我的生活陷入巨大的危机。一九九九年迫害以来,无数次的传唤,骚扰和非法对待,无法使我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中共散播的铺天盖地的谎言,绑架了不明真相的人,他们把愤怒和敌视投向我,使我的生活倍感压力。五年的监狱迫害,二次的洗脑班迫害。
监狱的几年生活,度日如年,与世隔绝。我无法想象是如何度过这段不堪回首的岁月的。以至在以后的生活中,夜里经常梦到在监狱里被迫害的痛苦时而惊醒。带着苍老的身躯(头发已严重脱落,腰部受损,脸色苍老)和受摧残的心灵离开监狱时,一时竟无法适应正常的社会生活。
离开监狱后,原本以为能够过上安静的生活,但只要我依然信仰法轮功,中共当局就让我的正常生活无法保证。我的电话仍然被监听,进出小区,都有门卫记录下我的出入时间,甚至监视我的行踪。随时可能被传唤和骚扰,随时都有可能被绑架进洗脑班或监狱里进行迫害。后来先后两次被绑架至洗脑班进行长时间的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