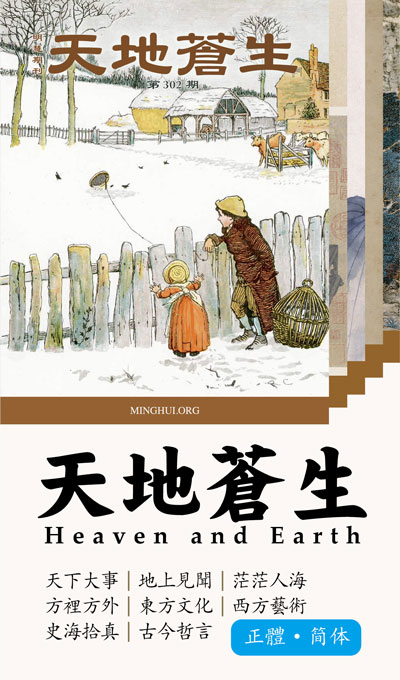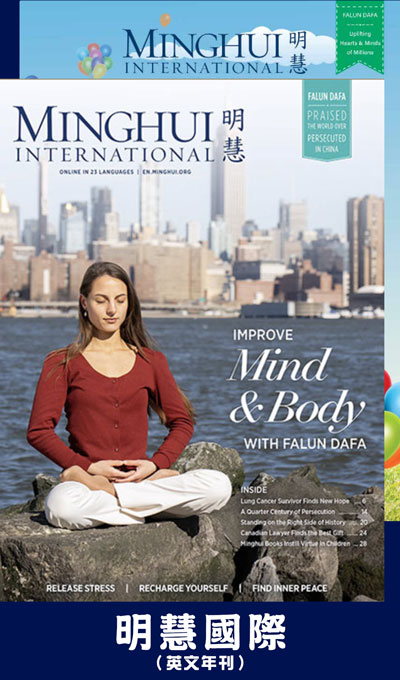辽宁女子监狱灭绝人性的暴行
从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后,中共对法轮功迫害开始了。我坚持炼法轮功,按“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说真话,曾被中共多次绑架、抄家、拘留、判刑。先后被关押在黑山看守所、沈阳看守所、辽宁女子监狱,遭到了惨无人道的迫害。
恶人举报,五年冤狱,酷刑摧残
零五年三月十五日,由于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我被中共不法警察抓到派出所,后被劫持到看守所,之后中共法院非法对我判刑五年,把我劫持到辽宁女子监狱。从此伴随我的是非人的折磨。
一、强行洗脑
因为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以后,监狱已被中共沦为专职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魔窟,恶警纵容、怂恿犯人迫害法轮功学员。在所谓的“人性化管理、依法治监、以法治警”的幌子下,卑鄙、无耻的指使犯人干了他们想干而又不敢明目张胆亲自去干的事。他们先给犯人施压,不按照狱警的意图做就不给记分减刑,视为改造得不好,恶人毫不掩饰地说:“打死你,象踩死个蚂蚁,你家人连尸首都看不见,只能抱着你的骨灰盒,你要明白这里是什么地方,这里没人给你出证,你没处讲理。”
走进监狱大门,我就喊“法轮大法好”,被后边看大门的恶人踢一脚。当时女子监狱关押三千五百多人,平均每十个人中就有一位法轮功学员,每位法轮功学员配两名夹控犯人全天二十四小时监视。七、八个人按着我强制穿劳改服,我拼命的反抗,她们扒光了我的内衣,把内衣收走,我只好穿劳改服。夹控犯人常年脱产,都是心狠手辣的打手,她们自称“专业户”。“专业户”对迫害法轮功的手段积攒了很多损招。
迫害的第一步,洗脑。放天安门自焚伪案录像、诽谤法轮功的资料。背监规。早上六点半出工,把我关在警察更衣室或空闲的值班室。晚上九点收工,关在犯人存衣物的库房或晒衣房或活动室,夜间12点上床睡觉。上厕所,洗漱,睡觉吃饭都是隔离状态。出收工的路上都是走在大队伍的后边,因我看见人群就喊法轮大法好,她们就堵我的嘴,打嘴巴,有时候把我打倒在地,后来就不让跟在大队伍的后边,等路上没人时,才放我出来。夜间我炼功,被恶人用手铐铐在床的铁栏上,一夜不让睡觉。我给夹控犯人讲法轮功的好处,善恶有报的法理,她们不听。
所谓的转化学习持续了七十七天,不见效果,恶警把我调到了最邪恶的二小队。调来两个全队最邪恶的犯人,一个叫王春娇,是长春人,是诈骗偷盗犯,一个叫苗淑霞,是抚顺人,是诈骗犯,她们心狠手辣。从第七十八天开始不再学习,以背监规为借口,隐藏杀机,找茬动刑。我不背,她俩动手打我,恶警李影过来问我为何不背监规,我回答:“大法弟子不背监规。我们不是犯人。”
二、手脚指(趾)甲扎插针
二月二十八日夜晚大约十点来钟,夹控犯人王春娇和苗淑霞露出杀手凶相,向我交代说:“今晚你是死是活,我俩说了算,打死你,象踩死个蚂蚁,你家人连尸首都看不见,只能抱着你的骨灰盒,你要明白这里是什么地方,这里没人给你出证,你没处讲理,放明白点,别让皮肉受苦,我们对付你们的招数有的是,不服从今天开始就没有你的好日子过,给你十分钟考虑时间。十分钟之后,我们听你的答复。”
十分钟之后,她俩回来了,问我考虑好了没有?我坚定的回答:“没什么考虑的,修大法就是心坚志不移。”这时,王春娇喊田素梅的号子(看监舍楼道的叫号子)准备好了没有?田号子拿来象水果大柚子一样大小的两团布绳子(给犯人晒衣服用的,是用布条子拧成象手指粗的绳子)把我从晒衣房带到库房(犯人存放衣服的屋子),夹控犯人王春娇用这布绳子从我的肩头一圈一圈捆绑到脚脖,把双脚固定到货架的下边,把脖子固定到货架上边。
然后拿出缝衣服的针,往我手脚趾(趾)甲里插针,都说十指连心,我尝到了扎心的痛!把针扎进去摇晃,等血浆凝固再找原针眼重复扎,恶人一遍一遍的扎,鲜血一滴一滴的滴在劳改服的裤子上,一滴一滴的滴在地板砖上,屋里就我们三个人,没有一点声音,好象屋子里没有人一样空荡荡的,田号子推开房门说,“到点了,都十二点过五分了。”这时我就不省人事了,晕了过去,有人大声说,送医院吧,没有担架啊,看我不行了,才把绳子解开了。后来我又明白过来了。这次扎了足有两个小时。再后来,只要不听她俩的就是随时扎。
在身上乱扎,当时新年刚过,人们还都穿过冬的衣服,恶犯人为了扎针方便,没收我的棉衣,只让穿毛衣套单囚服,恶人苗淑霞说扎脑袋吧,看不出来针眼,她俩就在长头发的地方乱扎起来,我就觉得凉飕飕的血在往下淌,用手一摸头发湿了,血止不住的流到脖子上,衣服上,她俩用手纸按淌血的血管,按了一阵,不流血了。我用手一摸,有个硬包。(据说大连庄河法轮功辅导员刘丽华死于这个王春娇的手上,她用锥子扎刘丽华的手指甲扎死的。)她俩连续扎了我一个月左右,又用防寒用的脖套,勒我的大脖子,拖着满地走,不一会就不省人事了,象被勒死了似的。过了多久我不知道,当睁开眼睛,也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也不认识人,过了好长时间,才明白过来。
灌辣椒水
这两个恶人一早上就用我的洗脸盆打来半盆开水泡红色的小朝天椒,又加了些盐,到晚上十点多钟犯人睡着了的时候,就在这个库房用泡好的辣椒水往我嘴里灌。我小时候听老人讲,日本进东北,用辣椒水灌东北人,灌的七窍流血而死。我紧紧的闭上嘴,她俩就拳打脚踢,把我打倒在地,恶人一只脚踩着左脸,右脸贴在地上,我的嘴巴踩开了个缝,另一个恶人趁机往嘴里灌,我在地上连滚带踹不停的挣扎着,一下就把盆打翻了,她俩气急败坏的说:撒啦再泡,再灌。继续灌还是灌不进去多少。
恶人王春娇出了损招,用辣椒水洗臀部,再把洗臀部水让喝二十汤匙,把打撒在地上的辣椒皮塞进阴道,再后来打来盆凉水,从脖领灌凉水,直到棉袄棉裤灌湿,再用手拍打拍打棉衣,灌到往下淌水了为止。光着脚丫穿拖鞋罚站在一块长宽三十公分的地板砖上,不许动,再把北窗南门打开让北风吹着我,两个恶人折腾累了,进屋睡觉去了。把我交给一个姓李的号子,看着我,李号子进来了,当着两个恶人的面打我六个大脖溜子,一直站到犯人五点半起床才离开库房,
接着两个恶人每天都是在犯人收工前或收工后把棉衣灌湿,在库房通宵罚站,门窗对流,再让我冻着,连续五昼夜之后停半宿,接着又持续两天,昼夜穿着湿衣服,又不让睡觉,当到第五天的夜晚十点前,我趁犯人还没睡觉,就冲出库房的门跑了出来,大呼“救命”,有的犯人吓的扔下盆往监舍躲我,我被两个恶人拖了回来。关上房门一顿暴打,这次肋骨打折了,不敢大出气,嗓子眼有粘痰,咳嗽,大小便肋疼,不敢迈大步。
警察上班把我带到监外医院拍片子,确诊软骨大面积损伤,我问为什么这根肋骨一按就咯噔咯噔的响,他们谁也不回答我。管福利的大牌牢头,拿来护腰脱病的人东西给我缠腰,把肋缠住,这样可以坐着躺着休息,过两个星期,恶人把保护肋的东西抢走,白天让我在监舍站着,夜间可以睡觉,当到半个月后,恶人王春娇趁我没有防备,猛抓我的头发往墙上撞,我口吐白沫头昏迷,我知道这是轻微脑震荡,这意味着有计划的新的一轮迫害又要开始了。
卑鄙下流的迫害惨无人道
掐,拧,拽乳房或乳头,掐大腿内侧,踢大小便,乳头被揪拧掉了皮,冒出了黄油,粘在衬衣上,一遍又一遍,是人难以想象的痛苦,我挣扎着,大声喊救命,两个恶人用胶带十字形粘我的嘴,封上嘴不让喊,用宽胶带把双手背铐的姿势绑上,把窗帘拉上,掐两大腿内侧也是非常痛的部位,皮肤呈黑紫色,如同大荷花的叶子,肛门、小便被踢的也是呈黑紫色,小便肿的和肚子一样高,撒尿和大便都困难,大小便一用力,肋骨也痛,这样极其惨烈毫无人性的折磨是持续的重复着,折磨的叫你再痛上加痛中煎熬着。扇嘴巴更是家常便饭,打得脸变形了,青紫色,暗紫色,象老松树的皮,两个恶人说不敢看,说象鬼一样吓人。把我打成这样子,恶警小队长李影和恶副区长董芳(专管迫害法轮功的)回避我不让看见她们,我要求见她们,两个恶人阻挡。
有一天恶警小队长李影拿着本子来了,客气的让我坐下,问我还好吗?她觉得到火候,可以做转化谈话记录了。我向她诉说两个恶人的暴行,她漫不经心的说:“你说这个打你了,那个打你了,谁看见了?你找个证人吧。”说着我把裤子脱到膝盖上,让她看,我说:“这就是证据,不用找人。”接着我就给她背零六年二月十四日司法部对监狱,劳教所,看守所下发的对警察六条禁令,第一条:禁止殴打或指使他人殴打,根据情节要给警察处分,恶警李影小队长气急败坏的说:“你还配谈六条禁令,”夹着本子摔着门走了。
由暴力酷刑转入漫长无休止的体罚
从五月十七日起昼夜罚站,连续四十一天,不让上床睡觉,罚站时不许身体靠着什么,不许走动,不许洗漱,洗衣,吃饭时只能蹲着吃,吃饭时间十分钟,房间没有表,她俩随意说几分钟就几分钟,我没吃完或刚端起饭碗还没吃一口呢,就说时间到,菜汤,米粥就被踢飞了。不许洗碗,不许自己打饭,两个恶人换班打饭。不能正常上厕所,三天五天不让上厕所,最长十三天不让上厕所,大小便只好憋着,每天只好不吃不喝,恶人告我绝食了。到六月二十三日,家人来探监,前一天晚上才让上床睡觉,洗漱一次。
六,人格侮辱,精神摧残
延续文化大革命时的一套整人侮辱人格的伎俩,拿记号笔在脸上写字,用纸壳写××罪挂上牌子,让我光着脚站着,把我的两只鞋又挂在我脖子上。挂完鞋之后,骂脏话,骂个没完,骂累了,然后又往脸上写出了花花样的字句来,两个恶人笑个不停,笑弯了腰,捂着肚子笑。恶人苗淑霞说:“老太太的脚丫子长的挺好看。”说着恶人伸出一只脚踩在我的右脚趾上,使劲的踩,后来苗淑霞两只脚上来拧着踩,大脚趾甲踩瘀血了,半年后,脱落下来,变成了灰指甲。
两个恶人在恶警的策划下,在施暴的时候,最让人难以承受的人格侮辱,把你打倒在地,痛的起不来时,逼着骂着打着让起来,勉强站起来,还没站稳,又一脚踹过去再爬起来,再踢,羞辱难耐的精神伤害超过法西斯,恶人王春娇往我的水杯里吐痰,往菜汤里吐唾沫,骂我本人连我的家人也挨个骂,咒骂性的骂人真是恶极了。这两个恶人就是这样不断的折磨我一百八十八天。
到了零六年的八月二十九日,换了位副监区长叫郭晓锐,新换了两个夹控犯人,一个叫张爱红(沈阳市人),另一个叫崔静(抚顺人)。开始时装伪善。九月初的一天,带我去狱里610办公室,这时我脸上的青紫斑痕,还挂在脸上呢,去见一位被转化了的法轮功学员,她也一口一个师父的叫着挺亲切,透露出了她的无奈,不得不低头的表情,劝我暂时忍屈辱过这关,我听不下去,大声对她说,住嘴,你不配叫师父,师父没教你这样委曲求全,三个警察有意安排的我俩在屋随便说话,她们在走廊遛呢,三个警察一听话不投机,慌忙进来,就把我带回监区。
伪善到十月十六日,夹控犯人张爱红说;“对你好也不行,对你不好也不行,你是软硬不吃,你想咋的。”说着脚就踢过来了,张爱红吼着说:“站着”,鞋和袜子被扒下来了,在警察更衣室站着,后来就在监舍三楼东侧的晒衣房,搬来带上下铺的两张单人床。又一次单独监禁我了。开始让我画押签字,她俩握着我的手强行签字,我不配合,把她俩准备好了的“转化书”划破,恶人张爱红气急败坏的抓起圆珠笔就往我的大腿内侧一气扎了七个窟窿,血止不住的流下来,从夜间的十点多钟流到天快亮了,这一夜只穿裤头,而且上身用浸湿了的内衣围着乳房站着,窗户门开着,把她们写好的转化书放在窗台上,说签了就可以解除惩罚,我光着脚面朝东站着,南窗东窗,北门大开着,这时已是十二月的下旬,两个恶人屁股靠着暖气,隔着玻璃窗监视着我。一会进屋来摸摸我露在外面的肩膀说,冻出字画来,嘴唇也紫了,一会又嘲笑的说怎么又冻红了呢。
在十二月六日到十二月二十二日期间罚蹲三天三夜;不让大小便持续十三天;用夹胸牌的钢夹,夹两个乳头;不让洗漱;两个恶人把我带到厕所,她俩一人尿一泡尿,不让我尿,然后拿扫地笤帚,蘸她俩尿的尿往我的头发、脸、内衣刷尿,刷的尿从头发上又滴到了身上,皮肤也是尿的骚臭味,然后再回房罚站,等衣服干,再重复,就这样一共四次,从早上一直到晚上吃饭。我向别的犯人要口水喝,恶人把我弄到水房,把门一关,她俩暴打我,被路过门外的一位老年人听见打我的声音,开门进了水房,怒视两个恶人,她俩住手了。
零七年三月末的一天,我要去洗漱,被恶人张爱红扇嘴巴,双手掐嘴巴,狠狠的抓左右脸,把我的右脸划开两条深浅不一的大口子,血止不住流下来了,半个多月了,伤疤还是没愈合好。副狱长,人称房政委来监区,我高喊冤枉,她把我叫到办公室,我就跟她进了办公室,她说你就这样进来了,为什么不说报告词呢?我说我没罪,我历来都不说报告词,我进来了就是冤枉的,你看我的脸,被她们挠的伤疤还在。我说:我提两条要求:一,调换小队。二,要求给违纪犯人处分,向她反映了一大堆迫害我的事实,她说她先回去调查了解一下。
接着我写了一份控告信,控告五个恶犯人,一是把腿打瘸了;二是肋打折了;三是脸上挠出伤疤,贴好了邮票准备寄出去。小队长李影说:“这类信她没有权利寄邮,只能转给监狱长。”当我碰到副狱长时问:控告信寄没寄?她说:这类信不给寄,就这样给压下啦。
零七年四月末,家人来见我。这次孩子们见了老娘的样子都哭成泪人了,我已经没有眼泪了。我跟孩子们讲了在监狱中受到的各种酷刑及迫害我恶人的名字、家庭住址。孩子们伤心极了。
接见结束后上至监区长,下到小队长,五、六个恶警对我进行轮番轰炸四个多小时。问我为什么告诉家人,问我想干什么?我说:“这些都是事实,不是我说出来的,是你们做出来的,我说出来了,是怕你们杀我灭口,以后就是我死了,家人心里也明白,他们的娘是冤死的,被打死的。”
我作为大法弟子,知道行恶者的下场,她们是在中共的唆使下无知的干着害人害己的勾当,她们才是最可悲可怜的。也使我感到了救人的难度和紧迫感。
我经历人生的风风雨雨,最剜心透骨的经历是:如今的社会为什么做好人这么难?好人为什么要坐牢房,好人为什么没有生的权利,没有了信仰、言论自由。例如: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之前,老百姓说法轮功好,政府也说法轮功好。我也学了,我也炼了,真的是好。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之后,老百姓说好,中共就是开始打压,再说好就犯罪了。这就是中国人的悲哀,中国的现实社会,身为中国人,就没有生命的选择了吗?法轮功强身健体、教人向善,是东西方人所共知的。中共邪教不会长久,对法轮大法普天同庆、同颂、同祝的日子会很快到来的。
English Version: http://en.minghui.org/html/articles/2012/8/8/13485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