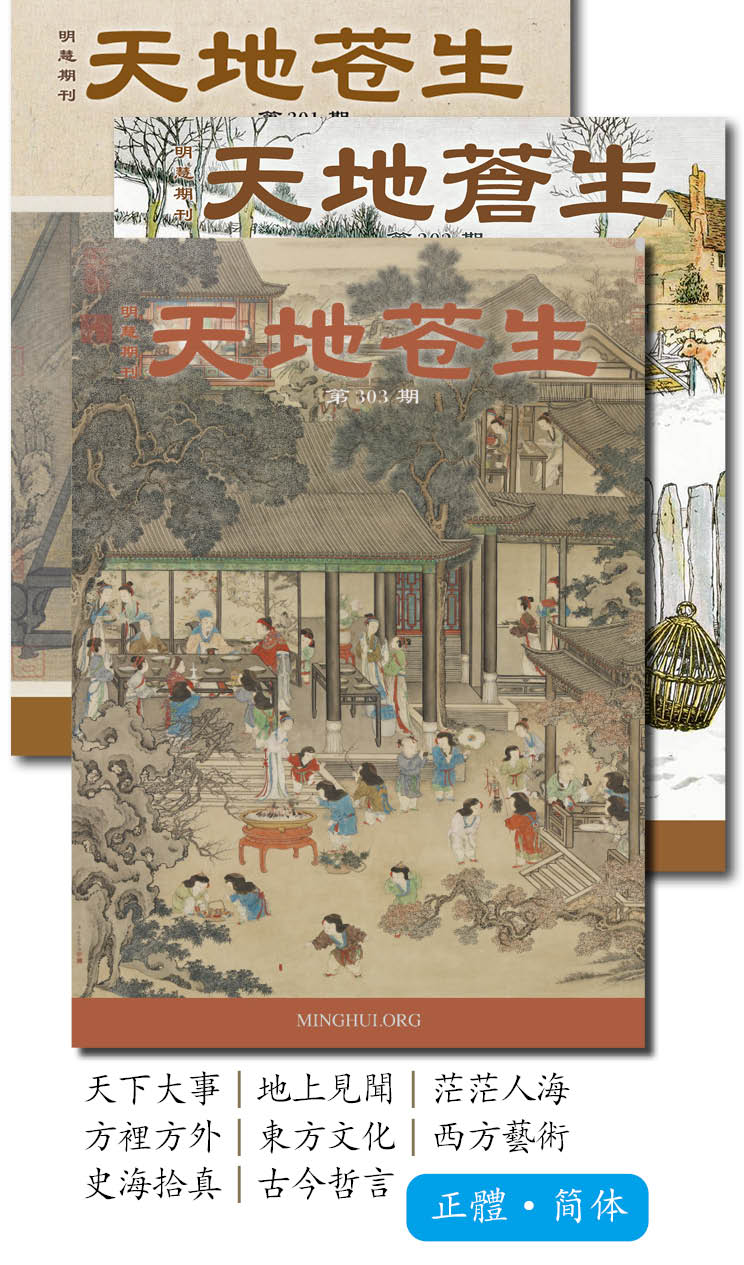二零零零年北京护法记事
(一)历史的一刻:二零零零年十月二十六日
二零零零年十月二十六日,又一个不平常的日子。天安门广场内警车遍地,警察、军人、便衣(特务)盯着过往行人,东侧博物馆的门前一长溜的停放着几十辆待命的大型客车。广场内似乎也比往日肃静了许多。我坐在旗杆东侧不远处的华灯柱下,等待着那期待已久的、庄严的一刻。
人越来越多,我的视线严重受阻。我踱到西侧的华灯柱下,内心静的出奇,只是一个劲的背经文。突然,广场南端孙中山画像附近,一幅二、三截楼高、几十米长、宽大的大横幅拉起来了!同一刻,“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还我师父清白!”、“还法轮功清白!”的口号在天安门广场炸响。
几乎在同一瞬间,各种大法真相横幅标语,横竖不等,长短不一,或大或小,大的要一、二十人合打,小的只需一个高举的法轮功条幅,犹如朵朵红、黄花,刹那间开遍广场,“法轮大法好!”、“真善忍!”、“还我师父清白!”的呐喊如大海波涛,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响彻云天,震撼寰宇。
我记下了这历史的一刻:二零零零年十月二十六日十三时二十分!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场面,恶人们惊呆了,醒过神来,顾不得斯文与头上顶着的国徽,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对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法轮功学员大打出手了。山东一对怀抱几个月婴儿的夫妻被它们打倒在地,军用皮鞋在他们的头上、脸上猛踢猛踩,鲜血满脸,看不清从哪流出来的。男的一边拼命护着怀里的婴儿,一边高喊“法轮大法是正法!”
上至白发苍苍的耄耋老者,下至几岁的小法轮功弟子,几乎无一幸免,每个法轮功学员都同时被两个或多个恶人围攻毒打。只一会儿,天安门广场的青石板地面就留下了法轮功学员的滩滩鲜血。
就在恶徒施暴中,在广场的中央,又别有一番景象:一位细高个的女法轮功学员旁若无人的从大背包里把法轮功传单一把一把的掏出来向游人撒去,游人争相接着、拣着、看着。一伙恶人冲过来,大约二、三十人,叫骂着,气急败坏的向游人手中夺去,又弯腰去追赶那满地飘来飘去的传单。好几次,恶人同时追赶一份传单,咚!头撞上了,一边骂骂咧咧各自揉着撞疼的脑袋,一边继续追撵那一张张飘忽不定的传单,顾了这边顾不了那边,乱作一团。
女法轮功学员镇定的撒完了好大背包里的全部传单,前后约二十多分钟。这伙恶人才如梦方醒般的七手八脚把她绑架。
几个小时过去了。伴随着如血的夕阳,伤痕累累、尘土满身的法轮功学员被塞進了几十辆大客车。地上的恶人对着步话机声嘶力竭地狂喊:快派车、快派车,不够用。
这一天在北京,数以千计的法轮大法修炼者被投入监牢,他们来自西藏、新疆、云贵、海南岛、黑龙江、南京、北京、上海、中原……他们来自华夏大地的四面八方,其中还有很多没出过大山,没见过火车的人。
(二)狭小囚室关押了三十多人
随后在刑讯室,一间挨一间,手铐、脚镣声、惨叫声、恶警的叱骂声,不绝于耳。尤其夜半时分,恶警为了往上爬,为了那带着血腥的奖金,它们加班加点,一个个酒足饭饱后,涨着猪肝一般的脸,喷着酒气,瞪着布满血丝的眼睛,手里提着刑具,在漆黑的夜晚,在惨淡的灯光下,在阴森的刑讯室里,真仿佛撞见了可怕的无常、狰狞的魔鬼。
遭受酷刑后,我被三个恶警拖回牢房。我支撑起来背经文,为随时而来的下一次考验做准备(那时悟性太差,只知承受,消业、过关,还不知否定旧势力)。我背着背着,突然一幅画面呈现在我的面前:林立带血的刀山、烈焰滚滚的火海、翻滚的油锅。我震惊了。
我被非法关押数月了,每天都有大批法轮功学员被抓進来,又有大批法轮功学员被送走,不知送往何方,竟无一日空白。尤其每日傍晚和夜半都被数次叫起来报数,刚刚被抓的法轮功学员到了,这是惯例。
大牢内早已人满为患,一间仅容纳十几人的狭小囚室,现在要关押三十多人,就象罐头中的沙丁鱼挤挤压压,尤其睡觉时床上地下都要一颠一倒侧身而卧,如果起来解手,就只能在窄小的便池处站到天亮了。
一天夜里,我又被拖出去审问,我依旧谈迫害,谈申诉无门,近一小时,一个警察站起身走了出去。这时,另一个警察对我说:“你们的师父太伟大了,他有你们这样的弟子真了不起!”
我对他说:“记住善恶必报,心里默念大法好,要善待法轮功,尽你的力量保护法轮功吧!”他点了点头。他又突然站了起来,啪!向我立正致军礼(他着装,头戴警帽)并说:“向你致敬!”
我知道他是在向师父致敬,在向大法致敬!一个警察得救了。
这里所有能关人的地方都被腾出来装满了法轮功学员,仍旧不够用。有传说江鬼拨巨款要在大沙漠无人区建造集中营关押迫害法轮功学员。
(三)一个堆满了横幅的房子
一天我突发奇想,一心想到天安门广场,再亲眼看一看大法弟子护法的洪潮。第三天大清早,两个警察给我戴上了手铐,押上警车,呼啸而去。我以为迫害升级了。
一个人要是没有了生死的概念,别提活得多轻松了。“走吧,这里的洪法任务完成了,师父又安排我去新的人群中洪法了,我会做好的。”我想着。
突然开车的警察对我说:“你跟着把你那天打的横幅找出来,量刑用。”接着大骂,“又不是领导,也管不着我们,连处长还没说话呢,这么冷的天,他倒非逼着我们去天安门找什么横幅,那横幅多了去了,你找得过来吗?”
我的心跳起来了:师父以这种形式带我去天安门广场了!我铐着的双手在胸前向师父合十致敬。
我被带到一座类似影院或剧场的大型建筑内,这里每道门都有持枪警察把守。我已由刚来时的满头青丝变成了苍苍白发,并且又被铐着双手。即使如此,它们仍然如临大敌,每道门我都被反复、仔细的搜身,我觉得它们很可笑,又很可怜。一通繁杂的手续后,進入一个至少二层楼高,异常宽大的大房子内。
这里堆满了横幅,几十米长,乃至几米长,粗细不等的大、中、小木杆、竹竿,如果不是这样大的房子还真放不下这么长,这么多的东西呢。屋里到处堆满了装得鼓鼓的大编织袋子,大的周长要至少三人拉着手才能合围,小的也得两人拉手才能合围,里面装满了法轮功条幅,然后一袋袋摞上去,直到天棚。他俩看了一眼,又大骂。在这里要想找出我当时打出的那个横幅无疑是大海捞针。我得以近距离仔细观察这些珍贵的东西了,大的已无法丈量,小的仅半尺多长,一幅幅都是崭新的红、黄颜色的布、绸或缎制作,还有不同风格的针织、刺绣、编织和我尚不知晓的其它缝制方法制作而成的,单是刺绣就有许多种不同的针法、手法。
我看着,轻轻的抚摸着:针针都浸透着对师父、对大法的真情,线线都绣着弟子归真的心,每一个条幅都是一件不可多得的、顶级的、珍贵的稀世文物!在这里,我真的出乎意料的找到了我当时打的那幅超过一米多长、二十公分宽的红地黄字“真善忍”横幅。我仿佛又回到了那激动人心的一刻……我又小心翼翼的卷起了它,轻轻的放回原处,“我要第二次再来天安门看你!”我心里说。
太阳已西斜,早已过了午饭时间,他俩又饿又累又气,骂着,擦着汗,随便拣起一个条幅,对我说:“就算这个吧,这么多,上哪找!”几个小时,只翻了冰山一角。
办着同样繁琐的手续,看得出来,他俩勉强耐着性子,打着精神,对他们装出一副毕恭毕敬的样子。经过了至少五、六个关卡,终于走出了大门。
车开了,我请求师父让车慢行,绕完广场。警车缓缓的向天安门驶去,到了金水桥,我戴着手铐,双手合十,高高举过头顶,向着天安门广场,用我的生命高呼:
“法轮大法好!真善忍!法轮大法是正法!还我师父清白!师父啊,放心吧。它们可以关了我的身,但它们永远关不了我的心,我为大法而生,我为大法而死,什么都改变不了我,大法,我学定了,师父啊,放心吧!”
我声泪俱下,眼泪就象那断线的珠子,湿透了我的衣襟。在这一、二十分钟的时间里,除了我的呐喊,好象一切都静止了,两个警察被震住了,如木鸡一般。
车快到西单了,我的目光从广场移过来,并慢慢放下高举过头的双手。车加速了。我决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洪法机会,我谈大法真相,我谈善恶有报,我希望他们留后路,不被淘汰。突然一个急刹车,他喊起来:“你骚扰我,差一丁点就追尾了。”
(四)放下生死度众生
邪党在大牢内对于法轮功学员的所谓“转化”,荒谬至极,只要骂一声师父或骂一句大法,当即释放,不需任何手续。反之,酷刑折磨和无根据的随意判刑。我问:“我修炼大法前动辄骂人,现在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只有大法才把人真正改变成好人,怎么××党非要把好人变成坏人才肯罢休呢?”警察说:“没办法。我们知道真善忍好,是江××逼着干的,谁不干谁下岗,家里老小吃什么?”他们被迫出卖着自己的良心。
在这里,我也听到很多警察在高压下,自动放弃高额的金钱和丰厚的物质利益的引诱,不肯泯灭天良,自动辞职了。
对于无昼夜无休止的酷刑“转化”,我决定绝食了。那时一人绝食,全号不准吃喝,刑事犯怕极了,他们要保护身体熬到出狱呢,所以对绝食者,往往同号的刑事犯会首先发难,大打出手。为了减少对同号刑事犯和同修的牵连,一天下午大刑后,我向全号三十多人大声讲(号内不准说话)我绝食的打算。一下子冲过来一帮人,揪住我的头发,按住我的手脚,把我掀翻在地。
我给他们讲我修炼前后的身心变化,法轮功蒙受的不白之冤,我進京的准备。他们低下了头,有几个哭了。牢门外狱警杂沓的脚步声、说话声,尽管我声音洪亮,但没有人制止我大声的洪法。
傍晚,我又被提了出去,走到门口,我回身说:“快学法轮功吧,做个真正的好人,永远不会犯错误。永别了!”我笑着招了一下手,当铁门在我背后重重的锁上时,我听到囚室内传出压抑的哭声。
我被押着七弯八拐的走了很久(这座地狱的内部似乎是呈放射状或蛛网式迷宫样的建筑结构),警察问了几次路才把我带到一间宽大的办公室里,高台上坐着七、八女狱警,桌上摆着桔子、苹果、草莓,地上坐满了曾经非法关押过我的所有囚室的刑事犯中的一部份,他们每人手里都拿着一个苹果一个桔子。我坐在他们事先准备好的小凳子上,看它们耍什么把戏。原来要我放弃绝食。我谈起了法轮功的一切。
屋里静极了,没有人走动,没有人说话,只我一人侃侃而谈,我谈了近一小时,在场的人全哭了,包括所有的女警察。我又谈到停止一切酷刑,不要助纣为虐,给自己留条后路和善恶必报的天理。我谈完了我要谈的一切后,一个女警察站起来说:“我叫(忘记了她的名字),是这里的领导,从现在开始,如果有人对你动刑,你马上找我,没有人敢阻拦你,我将直接严肃处理打人者。”
在这特殊的环境里,这群特殊的人仔细倾听并明白了法轮功,内心受到了震动,我已经达到目地了,个人的遭遇早忘到了九霄云外,我宣布放弃绝食。话音刚落,屋内爆发出热烈的掌声(除我外,全体鼓掌),几个警察和几个刑事犯同时不自禁的大声说:“大法好!大法好!”
我的心甜极了。我被披上了一件厚厚的棉大衣(我的衣服被恶警扒扔了,扬言冻死我),然后站起身来,有两个警察前面带路,在我的身后是一长串排列整齐的刑事犯,几个女警察压后阵,一路浩浩荡荡,逶迤而行。
途中很多警察跑出来看,一个男警察说:“谁这么了不起,在这里还这么威风!?”另一个声音说:“除了法轮功,还能有谁!”
一股热流刹那涌遍我的全身,我知道这是师父的安排,这是师父对我的呵护的鼓励和对这特殊人群的慈悲救度。我再一次的流泪了。
(五)她闯出了人间地狱
一天傍晚,杂乱的脚步声由远而近,牢门被打开了,五、六男警抬進一个四十多岁的人,扔到地上扬长而去。刑事犯惊呼:“是法轮功!”
躺在地上的人已不能动了,两支裤管被从下一直撕到裤裆处,整个大、小腿、脚乃至脚趾都是清一色的紫黑,从脚脖到大腿根肿得一般粗,像两个长长的黑木桶,已肿到了极限,好象再肿一点点就会皮肉迸裂,惨不忍睹。
她说一帮警察毒打她,打累了,把她按在地上,用两根大木杆横架在她的两腿上,四个警察站在木杆的两头上下压油(跷跷板),还说看到底谁硬?
她绝食了,迫害也随着升级:先是指使刑事犯按住往嘴塞;继而插管灌食;砸上手铐、脚镣也无济于事;它们将手铐、脚镣紧紧连在一起,她肿得紫黑的腿不能弯曲,只得弯着脊背,痛苦不堪。即使这样,还要每天被拖出去长时间的折磨和野蛮灌食,她都想尽办法抠吐出来。
二十多天过去了,恶警除了打死她,再无计可施。
一天半夜,突然闯進五、六个男警察,打开她链在一起的手铐脚镣,“处长”递给她一张去河北廊坊的火车票,让四个警察用警车把她直接送到火车上,并告诉她永远不许再到北京来。她笑了,笑得那样天真,那样灿烂,虽然她没吃没喝,腿、脚仍然乌黑肿胀,但却一直红光满面,光彩照人。
她站了起来,健步如飞。那群警察面面相觑,目瞪口呆,他们原以为要抬着走呢。她闯出了人间地狱。
English Version: https://en.minghui.org/html/articles/2006/10/26/7933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