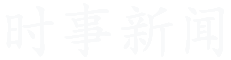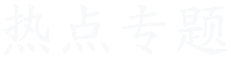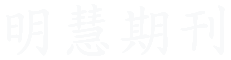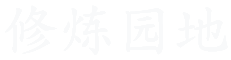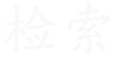国安大队三万圆装备刑讯室 “打得再狠外面也听不见”
第一次是在2000年3月的一天,我爱人的几位朋友(功友)来我家玩,我不认识他们,他们当天就走了。结果被恶人举报。第二天,厂里就向A市C派出所报告了此事。警车开来,不分青红皂白,野蛮地抄了我的家,抄走几本大法书和师父的法像,把我绑架到A市看守所八号牢房,非法关押了二十五天。
进去那天就惨遭犯人毒打,强行把我身体摆姿势,当作桩靶,犯人轮流上场拳击胸部。手肘剁大腿,弯腰弓背,犯人站在高处用穿皮鞋的脚踢打腰背。在二十五天中有十多天都挨打。恶人毒打我的其原因一,是为了叫我喊家属多交钱,龙头老大等好吃好喝;二,是发泄他们的魔性;三,有个偷猪的关进来,他们叫我打他,我说我是修炼真善忍的,不打人,结果我被十多个人狠狠打了一顿。我的腰、背、手和腿脚肿得很粗,蹲不下,睡觉翻身都痛得咬牙。出来两个多月后,疼痛都未完全消除。
市看守所犯人打人成风,很多大法弟子和新进去的犯人都亲身领受过。警察不把人当人看,他们素质低劣、品质败坏,以“假恶斗”治狱。比如刚一进去,狱警就当面对犯人讲:“你们不要打人(明知打过人),但不守规矩的也得教训教训。”龙头及老滑头犯人就心知肚明该如何了。熟悉后,犯人们就讲:“挨了打不能告,最好是当面撒谎说‘没挨打’,否则回头打得更凶。”
第二次是在2001年3月18日,我爱人被绑架进了A市某洗脑班,厂里公安科问我:“法轮功你还炼不炼?”我说:“这么好的功法,哪舍得丢哟?”就被非法关押到派出所,第二天又送到洗脑班,对我进行了五个月的精神迫害,每个月缴贰佰元的生活费。其间,由于不去听诬蔑大法、诋毁师父的造谣和诬陷,有一次被罚晒太阳四个小时;又一次被警察张某某、郑某某打得趴在地上,踩胸部、铐手铐、打耳光。我爱人被郑踢了几脚。非法关了五个月后,我为抵制洗脑班的非法关押,绝食三天后,才放我出来。
第三次是在2001年10月13日,我去养蜂场拿一张大法真相资料给养蜂人看,被恶人向派出所举报。派出所所长胡某派人来搜去了那张大法资料,并把我绑架到派出所,铐在派出所的钢筋铁门上,左手往上拉伸吊起,又痛又麻,一会儿手就肿了起来,加之心里烦躁欲吐,极度难受,我大声叫着,但他们不予理睬,吊了我一个多小时。A市公安局一科李某某、周某闻讯又一次无搜查证非法抄了我的家,抄走炼功音乐带一盘,同时送我到M戒毒所非法拘留。三十天时,周问我还炼不炼,我说“炼”,因此周当场填拘留证,要多非法关我二十天。为反抗非法关押,我开始绝食,第四十八天,他们将我放出。强行缴纳伙食费每天五元。他们知法犯法成了家常便饭,心里哪有一点法治观念。
第四次是在2003年8月26日清晨四点多,我去某镇发真象传单,被当地派出所五个警察(三个便衣,二个身穿迷彩服)跟踪抓捕。我给他们讲:“我是修炼法轮功的,是好人,发传单是为了把人从谎言毒害中救出来。你们要知道真善忍好,善恶有报是天理!”一个警察说:“我不怕报应。”他们用麻绳把我反绑在电杆上,一个40多岁的长脸瘦警察眼露凶光,狠命击打我的胸部和软肋部,我大喊:“恶警打好人啦!打死人啦!”当我被打得头抬不起,腰往下弯时,恶警就趁机猛踢我的胸腹部,我顿时痛昏过去。
清晨五点过钟,派出所随车来了四名警察(包括所长),给我解绳锁上手铐,抬上车并掐按住我的后颈项,又抬下车甩在派出所沙发上,我口渴得舌头都转不动了。我当面指责“派出所警察打人”,他们公然在铁的事实面前矢口否认,抵赖撒谎都不脸红。
八月二十六日九点过钟,A市国安大队大队长李某和周某、王某某驾警车来到,把我拉到厂里我的住所,与此同时市公安局随车又来了两名警察,再一次非法抄了我的家,我不仅被锁上手铐,周还用绳索捆住我并牵着我不准进屋,同时狠命掐按我的颈项几近断气。我说:“你们无证抓人,无证搜查,知法犯法!你们放着许多大案、要案不侦不破,对付一个只为炼功做好人的人就动用了这么多警车、警察,你们惩恶扬善的警察天职哪里去了?”他们不理不睬,只听得屋内踢踢碰碰、翻箱倒柜的声响;他们进进出出,抄了一遍又一遍,接连抄了三次。
后来把我从厂里押到国安大队办公室,一只手用铐,一只手用绳,绑在一张椅子上审问,边问边打,边揪边踢、边掴,专门针对手、臂膀、脚腿和脸,这样刑讯逼供到吃晚饭,我的臂膀、腿肿得像泡粑一样,红一块紫一块。
傍晚,我被秘密关到酷刑室,一个警察说:“为装备这间屋就花了三万多元,现在好了,打得再响,哭叫声再大,外面都听不到,非常隔音。”他们强制我坐上老虎凳,锁上脚镣手铐,施用车轮战、疲劳战,把九个警察(据说有三人从B市调来,还说他们对法轮功刑讯有所谓“丰富经验”)分成三人一班,三班轮番拷打审问、刑讯逼供,点点滴滴反复追问,时刻拳脚相加。我说:“我肿得这样了,你们不要打我。”周说:“打死火化了就是!”在酷刑室,他们更加疯狂,丧失人性,他们视我淤血斑斑的手臂和腿于不顾,哪里痛就打哪里,哪里肿就往哪里揪、踢。在连续刑讯、拷打下,不仅使人疼痛钻心入骨,而且感到非常疲惫,眼皮不自觉地闭上,他们就按动老虎凳上的电钮发出刺耳的强烈噪声,还要使用冷水浇头浇脸,使我从昏迷中醒过来。这期间,大队长李某还要强制我一只手从肩上下去,一只手从后背反手而上锁上手铐,名叫“苏秦背剑”,我年龄大,体胖,骨头老化,弄得我眼泪直淌,声嘶力竭地哭叫才罢手。其后仍然坐老虎凳。这样刑讯到八月二十七日八点半钟,我被拉到国安大队办公室,恶警们按照头一天下午方式审问。审问人:大队长某、周某、王某某、胡某某等。
二十七日九点多钟,送往L看守所,所里负责人说:“你们把人打成这样,脚手肿得那么粗,上厕所都没法蹲下,这样的人我们不收!”又说:“你们不能随便打人,打人是犯法的。”还有个老公安也这样说。当时押送我的周、王都哑口无言。那个负责人停了一下又说:“要收可以,你们写个保证。”于是,周向国安大队汇报请示,改送A市看守所。
从二十六日四点——二十七日十点,恶警们连续给我戴手铐三十小时。
监室最多关过十七人,睡铺人挨人、脚对脚,除放马桶的地方外全部睡满人。只有两个小窗口,屋里热得满头大汗。监号里等级分明,水泥台子比下面的过道宽,但台子上只睡牢头等七人,而狭窄的过道上除摆着臭气熏天的马桶外,还要挤上十个人。从来就不会有开水供应,每天的两餐都是生米饭和看不到一滴油珠的白菜汤或土豆汤,而且从来都是米不淘、菜不洗,常见小白菜心里卷着卫生纸。
监号里打人成了常事,我炼功被打,不参与唱歌被打,不合他们的意被打。九月二十七日,龙头指使犯人说:“要二十四小时监视他,如果炼功,你们就给我蒙住被子乱打。”我说:“我要炼,炼功的都是好人,谁也没有资格管我。”结果被蒙住被子打,有犯人踢我下身,痛得我闭气。这一次,不法恶人将我非法关押了三十三天才释放。目前全身疼痛还未消除。